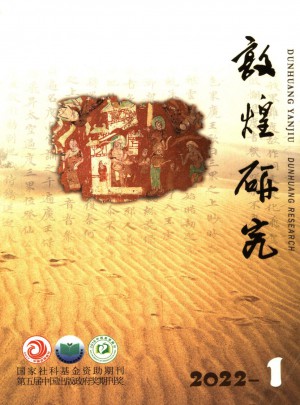引论:我们为您整理了13篇敦煌文化论文范文,供您借鉴以丰富您的创作。它们是您写作时的宝贵资源,期望它们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灵感,让您的文章更具深度。

篇1
一、对俄藏三件社邑文书内容的分析
社邑(社)是一种民间结社,属于中国古代民间基层社会组织。民间结社在先秦已有,到唐五代宋初已达到兴盛阶段,从敦煌遗书中保存的几百件该时期的社邑文书资料中可以全面看到它的发展。
有关社邑文书的研究,已有不少成果,20世纪30年代,日本学者那波利贞便有对唐五代社邑的研究,随后日本学者竺沙雅章又进行了研究。至20世纪80年代,国内学者宁可先生发表《述“社邑”》一文,既综合评论了前人的研究,又对社邑的源流演变发展,作了综合性的论述。随后宁可、郝春文整理出版《敦煌社邑文书辑校》一书,尽管没有来得及收入俄藏社邑文书,但它仍是目前见到的全部社邑文书之集大成者,有比较准确的录文、点校、断代和说明,为学者提供了一部系统翔实的资料,这是一个重要的成果。
近年又有郝春文、杨际平、孟宪实等先生发表的论文,而且在对社邑的理解和认识上,还有过许多的讨论,这些都有益于对社邑研究的推进。不过,这些讨论只限于英藏、法藏和国内所藏之敦煌文书,还未涉及到俄罗斯收藏的社邑文书。而俄藏的社邑文书则又可以给我们打开新的视野。
此前的研究,对于唐五代民间社邑的性质及功能,大多集中在丧葬互助、追凶逐吉等实用性方面。实际上社邑重要的性质和功能,在于教化人、熏陶人,它所教化的是儒家的纲常礼教、强调的是尊卑之礼。至于丧葬互助之类的活动,也是以礼为先,而后才追凶逐吉、丧葬互助的。就其性质而言,仍然是封建性的群众组织。关于这一方面,没有引起学术界的重视。本文拟针对这个问题,以Ⅱx11038号文书中的《投社状》为主,结合《索望社社条》、《社司罚社人判》的内容作些探讨:
(一)Ⅱx11038号社邑、社约文书的特色
投社状实即入社申请书,是社邑组织成立以后,要求加入者向社司提交的申请书。在俄藏axl2012号文书中有一件《后唐清泰二年(公元935年)三月王粉子投社状》,现释录文如下:
1.投社人王粉子
2.右粉子,贫门生长,不识礼仪。
3.在于家中无人侍训,情愿事奉
4.三官,所有追凶逐吉,奉帖如行。
5.伏望三官社众,特赐收名。应
6.有入社之格,续便排备。牒件状如前,谨
7.牒。清泰二年三月日王粉子状上(册5,第152页)。这是一件内容简单的投社状,是说自己不识礼仪,无人侍训,愿意人社参加社内的追凶逐吉活动。类似的投社状,已经面世的有六件,有的在内容上与本件相近似,如P.4651《投社人张愿兴王祐通状》载有:
右愿兴、祐通等生居末代,长值贫门,贪计社(邑),不怪礼节,今见龙沙贵社,欲拟投取,伏
乞三官收名入案,合有入社格礼,续便排备。特赐处分。牒件状如前,谨牒。有的在入社目的和要求上,略比本件丰富一点。如P.3198《投社人某乙状》(样文)所云:
投社人某乙:右某乙贫门贱品,智浅艺疏,不慕社邑之流,全阙尊卑之礼。况闻明贤贵邑,国
下英奇,训俗有立智之能,指示则如同父母。况某乙然则愚昧(以下原缺文)。
此件说的是自己缺尊卑之礼的教养,社邑可以如同父母一样能使自己去俗立智,故而要求人社。这些投社状,就其文字而言,一般都只有七八行,比较简单。
然而,在且11038号文书中的《投社状》,则与上述诸件的面貌有很大的不同。虽然此件在起首就标明是属“投社人某专用”的样文,却有文字22行,对于社邑的性质、教化的作用以及自己入社的愿望等等,均用典雅的文学语言来作表达,既形象又充分,可能属于供社会上层使用的一种投社样文。这对于我们研究古代社邑的性质、社会功能和作用,都有一定的价值。
社条是社邑组织的规约,在敦煌文书中也多有记载,按其性质区分,有城隍社、坊巷社、义社、亲情社、女人社、佛窟社、渠人社等,而规约按其结社性质的不同,在内容上又多有所侧重。x11038号文书中的《索望社社条》,则是以索姓望族所订立的社约,像这类以某一宗族结成的宗族社约,在此前尚未见到。它不仅丰富了敦煌社邑的内容,而且还为我们具体认识敦煌的宗姓社提供了具体的材料。
每个社邑都有自己的社条,但详略不同,有总则、结社目的、立社原因、违反处罚的具体条款等。立社之初制定的社条称“大条”或“条流”,也有的称作“祖条”,要封印保存起来,一般情况下不能开封,除非遇到众社难以裁决的大事才可开条。如果大条不完善或又有要增加的事宜,可另作补充规定。如S.6005《敦煌某社褶充社约》所载:
伏以社内先初合义之时,已立明条,封印讫。今缘或有后入社者,又未入名,……若件件开先条流,实则不便。若不抄录者,伏恐漏失,……遂众商量,勒此备案,……余有格律,并在大条内,若社人忽有无端是非行事者,众断不得,即须开条。若小段事,不在开条之限。故立此约。
这件补充社约就提到了大条、条流,并对开条之限也作了规定。值得注意的是“若小段事,不在开条之限”。又如x11038—7号《社司罚社人判》中所言“更有碎磨格式、偏条所录也”。这里的“碎磨格式”与“小段事”都是指琐细的款条,但在此《判》文中把琐细的款条称之为“偏条”。偏条是针对大条、祖条而言,由此得知社条有正条、偏条之分,正条又可叫大条、祖条,偏条则是对具体事作具体规定的临日寸.性社条。这是其它社邑文书中所未见者。社条对社邑来说非常重要,它对研究社邑组织的规约、活动情况有重要价值。
(二)社邑有教化人、熏陶人的性质和功能
俄藏x11038号文书中的三件社邑文书,更多地凸显了社邑在教化人、熏陶人方面的性质和功能。首先看投社状,没有姓名和具体年代,系投社状样文,样文包含了实用文书的基本内容,因为实用文书都是以样文为范本,它比实用文书应用更广、更具有代表性,它的出现乃至流行,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现实需要。
如前所论,此件投社状的内容比见到的其它投社状的内容要丰富,主要体现在投社人对入社的认识高了一个台阶,把所遵循的伦理道德提到更高的思想境界上来。入社的目的是要在社邑受到教化和熏陶,如一开始就写出社邑的宗旨是“布义贞松守节”,以“异累不辟、土奇诞质、义重二睦、立珍宗而约于时”,来对社邑作出承诺。接着说“断决三章,兢竹清而[载]其语;莲襟绝代,不违向化之心”。即把社邑的章程,都严肃认真一条条地写下来,即使同辈亲近者没有了,都不违背社邑的教化。“向化”二字,也道出了社邑的另一种功能,“化”是指的教化,向化,实际是指心向社邑的教化。用“家顺弟恭、实抱陈重之泰,忠父慈亲,不妄高柴之幸”来表达受到教化的功效。这是在说,尊崇了礼法条规,心中怀抱着陈重那种舍己助人、谦让重义的胸怀,就能迎来门第恭顺,家家昌盛,奉孝敬老。在亲情的扶持下,即使像高柴一类的庸才也能得到重用和好的境遇。这里道出了受教化的目的和巨大作用。又云:“既揽高仁、恳修传劫”,高仁,是指已有高水平仁义道德教养的人。既然延揽到这样的高仁者,就应恳修传劫,即把仁义道德和善良一代一代传承下去。尤其值得注意者,是“恳修”二字,“修”本身就是受教化,而且是“恳修”,还用典故事例来赞扬该社,如“成晓傲半千善业,医方置神街立向,”把社邑的教化用医方来作比喻。这种教化在敦煌社邑文书中多有体现,如:s·5629号《敦煌郡等某乙社条壹道》(文样)载:“亦资社邑训诲”12’(第36页)。即让社邑教诲、开导。P·3989《景福三年(894)五月十日敦煌某社社条》记:“敦煌义族后代儿郎,须择良贤,……”;“立条后,各自识大敬小,切须存礼,不得缓慢”。又S·6537背/3—5《拾伍人结社社条》(样文)云:“人情与往日不同,互生纷然,后怕各生己见。所以某乙等壹拾伍人,从前结契,心意一般。大者同父母之情,长时供奉;少者一如赤子,必不改张。”“济危救死,益死荣生,割己从他,不生吝惜,所以上下商量,人心莫逐时改转。因兹众意一般,乃立文案。结为邑义。世代追崇”;“亦要一人为尊,义邑之中,切藉三官钤锫”等。这些都进一步揭示出社邑进行温、良、恭、俭、让等礼教教化的功能及作用。
通过这件投社状可以看出社邑在当时是民众精神上的支柱,它是教化人、熏陶人的场所,其指导思想是儒家的纲常礼教。这在《索望社社条》中也有反映。这件文书全文21行,尾部残缺,没有具体年代,遗失部分条目和社人名单,是件实用文书,文中云:
今有仑之索望骨肉,敦煌极传英豪,索静弭为一脉,渐渐异息为房,见此逐物意移,绝无尊卑之礼,长幼各不忍见,恐辱先代名宗。
这里提出尊卑之礼没有了,宗亲关系出现松弛,造成的原因是由于家族渐渐地分家、开始追求物质利益,转移了思想感情。然而,长幼都不忍看到这个现状,恐怕有损于先辈的名望和宗旨。针对这个问题,于是制定了强制性的三条规约,以防止“已信後犯”、制止“所有不律之辞”,如“或若社户家长身亡,每家祭箍一个,著孝准前”。社户家长中,若有身亡者,每家都应送祭盘,从表面看,是个互的规定,其实际深层含义乃在于,强调血亲宗族关系,严格尊卑之礼,彰显孝道,故而强调“著孝准前”,即按原先的着孝规定办理。“更有贫穷无是亲男兄弟,便须当自吃食”;参与丧葬事宜的人,虽有贫有富,但这里强调的是宗亲友悌之情,即使贫穷,没有送祭盘,也应在一起吃饭。“齐擎攀不得踏高、作其形迹,如有不律之辞,罚浓酞一筵”;送葬对攀棺擎举要齐心,不得对攀棺者不亲近或不礼貌、作出厌恶和嫌弃的样子。如有不按规章的言行,罚浓酞一筵;“或有策凶逐吉,件若耳闻帖行,便须本身应接,不得停滞,如有停帖者,重罚一席”。如有依次逐个转行须办丧事或喜事的帖子,不得停滞,如停滞者要重罚一席等。用这些条约来规范、教化宗族的行为,目的在于加强索望族内部的亲情关系,维护族内伦理纲常的尊卑之礼,同时也是通过强制性的规约来实现社邑教化人、熏陶人的作用,从整个思想体系看,完全是封建性质的。
违反了社约就要受罚、棒打、甚至赶出其社。如且x11038—7号《社司罚社人判》就是带有强制性教化的手段,此件首尾残缺,主要条款基本完整,是件实用文书,从残存的九行判文看,有三种处理内容,第一种是:“妄生拗拔,开条检案,人各痛决七棒,末名趁出其社,的无容免。”这是社司对犯有无中生有、蛮横跋扈、不遵教化的社人进行“开条检案”,即把入社之初制定的社条开封,将章程规定的条款打开进行对照,对违约者痛打七棒,进行除名,赶出社外,毫不留情,这是一种处理。第二种情况是对于“兼有放顽不乐追社,如言出社去者,责罚共粗豪之人一般,更无别格”;即对不受约束,扬言要出社者,处理情况同处理“妄生拗拔”者一样,不另规定。第三种是对“更有社人枉遭横事,社哀憨而行佐助者,一任众社临事裁断行之,不可定准”;乃是指有社人发生冤枉或死伤的事,社人要有仁义怜悯之心,同心去帮助,对这类情况可酌情做出决定。除以上这些规定外,还有“碎磨格式,偏条所录也”。这是指琐细的条款,在偏条中都有规定。类似的处罚手段还见于S.5830《社司罚社人判》,此《判》残卷是实用文书,只存2行内容,但也能说明社邑对违反条规的人的处罚情况,如“准条案合罚酒壹瓮,合决十下,留附”,这是说按以前的条款规定,罚酒壹瓮,痛打十棒,留附在社内。这里表明社邑组织对社条的规定是严格认真执行的,而且一丝不苟,同时也表现出社邑的组织手段也是封建性的。
通过以上的社司判文,还能看出,社邑组织虽属民间自愿结合而成,一旦加入后,便有严格的行为规范,违背了尊卑之礼,就要受到严厉的处罚,这些都体现出了社邑是在用封建性的强制手段来贯彻社邑的教化。
这种教化在法藏、英藏文书中也有反映。如P.3198—2《投社人某乙状》说:“训俗有立智之能,指示则如同父母”。训俗,实指训化风俗,去掉鄙俗的东西。立智,乃指接受儒家思想教化,社邑在这方面的指教,如同父母的教育一样。S.6537背3—5《拾伍人结社社条》中也有言:
窃闻敦煌胜境……凤化人伦,籍明贤而共佐……人民安泰,恩义大行。家家不失于尊卑,
坊巷礼传於孝义……。
这里强调的是尊卑,是礼传于孝义,反映出社邑教化提倡的内容,其目的是“风化人伦”,是“恩义大行”。社邑在正面教化、熏陶人的同时,总是要辅之以强制性的手段,在本社条尾部,又规定:
局席斋筵,切懑礼法,饮酒醉乱,凶悖粗豪,不守严条,非理作闹,大者罚球腻一席,少者决
杖十三,忽有拗戾无端,便任逐出社内。立其条案,世代不移。
局席斋筵,实际也是社人的一种聚会,也须“切蜃礼法”,如果不遵礼法,就要受到处罚。P.3989《景福三年(894)五月十日敦煌某社社条》规定:
立条后,各自识大敬小,切须存礼,不得缓慢。如有醉乱拔拳冲突,三官及众社,临事重有决罚。立此条后,於乡城格令,便须追逐行下。恐众不知,故立此条。
这是在正面教化的同时,对不存礼的行为,根据情节的轻重给予处罚。s.5520(<社条(文样))中也有规定:社内人身迁故,赠送营办葬仪、车辇,仰社人助成,不得临事疏遗,勿合乖叹,仍须社众改口送至墓所。
这是对送丧礼仪的教化,这种教化是必要的,一户出事,众社人齐心帮助,体现了互助友爱的精神,并能加强社邑成员之间的关系,这也是维护纲常礼教的表现。
从以上几个方面都说明社邑有教化人、熏陶人的性质和功能,而且是辅之以封建强制性手段的教化。其教化的内容是忠、孝、仁、爱、温、良、恭、俭、让。其指导思想是封建的伦理道德,尊卑之礼,如“置社为先,弟互适奉尊卑,自后承传轨则”,“若不结义为因、焉能存其礼乐?所以孝从下起,恩乃上流”,“夫立义社,以忠孝为先,……尊卑须之范轨”,唐五代的社邑,正是靠这一整套封建伦理道德观念作为自己精神支柱的。
(三)社邑结社的目的是先尊卑之礼,后丧葬互助、追凶逐吉
在敦煌社邑文书中,对社邑的性质和功能有多种反映,如崇奉教化、丧葬互助、祭祀社神、设斋建福、修造佛窟、修渠劳作……等等,其中则以崇奉教化、尊卑之礼为首要功能,其它均为具体事务,这在俄藏社邑文书中表现得很明显。
X11038—5号《投社状》一开始就写有:“鸿(鸣)沙盛族平张,结号父子之乡,布义贞松守节。”反映出让义广布于他人、坚守贞松之节操是社邑的主要宗旨和意图。其入社的目的,就是为了“恳修传劫”,要把“布义贞松守节”的传统传承下去,以求得“家顺弟恭”、“忠父慈觏”的局面,在这里可以看出,它始终围绕着的一个中心思想,就是忠、孝、仁、义的纲常礼教。
《索望社社条》体现的主体思想,也是针对“见此逐物意移,绝无尊卑之礼,长幼各不忍见,恐辱先代名宗”而提出的,核心问题还是尊卑之礼。在此前提之下,再谈“社户家长身亡”等丧葬互助的事,即使在运作丧葬时,也要“著孝准前”,“不得踏高作其形迹”,严守尊卑之礼。在《社司罚社人判》中:“妄生拗拔,开条检案,人各痛决七棒,抹名赶出其社,的无容免。”这是对违背了尊卑之礼所受的处罚。
从法藏、英藏敦煌社邑文书中,也能看到类似的宗旨。如P.3989(<景福三年五月十日敦煌某社社条》中言:“今且执编条,已后街衢相见,恐失礼度,……立条后,各自识大敬小,切须存礼,不得缓慢”(第9—10页),仍然是以礼为先。在P.3730V《某甲等谨立社条》中对此说得最清晰:
敦煌胜境,地杰人奇,每习儒风,皆存礼教,谈量幸解言语,美辞自不能宾,须凭众赖。所以共诸英流,结为壹会,先且钦崇礼典,后乃逐吉追凶。
在这里,习儒风,存礼教,“钦崇礼典”等摆在主要地位,而后才是“逐吉追凶”,一先一后的次序,表述得十分清楚。前引P.3198—2《投社人某乙状》:“某乙贫门贱品,智浅艺疏,不慕社邑之流,全缺尊卑之礼。”道出了这位投社人是为了追逐“尊卑之礼”才来投社的,明显地衬托出社邑以教化为先的性质。S.6537背3—5《拾伍人结社社条》中“家家不失于尊卑,坊巷礼传于孝义,……所以某乙壹拾伍人,从前结契”。所谓“从前结契”,是指依据前面的不失于尊卑,礼传于孝义的宗旨而结社。
透过这些社条、投社状的内容,不难看出,尊卑有序、孝义传家等纲常伦理思想是指导人们结社的基础,也是敦煌社邑结社的灵魂。社邑结社首先强调的是尊卑之礼,而后才是丧葬互助、追凶逐吉等一类具体性事务。换而言之,社邑的丧葬互助、追凶逐吉等活动都是在伦理纲常思想指导之下进行的。
二、唐五代敦煌社邑对封建统治起着辅助教化的作用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封建统治者是以儒家的“礼”作指导思想的,荀子对礼的起源,曾分析说:礼起于何也?日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乎欲。两者和恃而长,是礼之所起也。
要使整个社会在物与欲之间达到一种平衡,就须用礼来加以规制。故荀子又说:
故礼者养也,君子既得其养,又好其别,曷谓别?日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
所谓“皆有称者”,就是尊卑有别。汉朝的师丹说:
圣王制礼,取法于天地,故尊卑之礼明,则人伦之序正,人伦之序正则乾坤得其位,而阴阳顺其节,人主与万民俱蒙秸福。尊卑者,所以正天地之位,不可乱也。
在封建统治者看来,尊卑有别乃是礼制的核心,可以正天地之位,正人伦之序。正因为如此之重要,故通常将“礼”的概念,形象而具体地称之为尊卑之礼。
所谓“人伦之序”,就是指的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这类关系,即五常的次序。如何来正这类关系的次序?用尊卑之礼、即用“三纲”来正,也就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提出三纲五常的目的,乃在于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稳定封建社会秩序,以达到天下太平,五谷丰登、社会安定。当然,这种安定是封建统治者的安定,正如唐太宗所言:
朕为兆民之主,皆欲使之富贵。若教以礼义,使之少敬长,妇敬夫,则皆贵矣。轻徭薄敛,
使之各治生业,则皆富矣。若家给人足,朕虽不听管炫,乐在其中矣。
人民遵守了封建礼制,就有了封建社会的规范和道德秩序,君王就能更有效地统治人民。社邑所教化的就是尊卑之礼,指导思想就是封建纲常礼教,这些正是封建统治者维护等级制度所需要的,而社邑正好起了辅助作用。强调尊卑之礼,就不能犯上,就不会反对皇帝,反对地方官和家长。在这个思想基础上,统治者的利益与社邑的宗旨是一致的。从这个角度看,社邑不仅对封建统治阶级统治人民起了辅助教化作用,同时为稳定封建社会秩序、稳定家庭、家族内部的尊卑关系也起到了维护的作用,这正是敦煌社邑在民间得以长久地生存和发展的主要原因。
唐朝政府对于这类民间社邑的态度,基本上是支持的。武德九年(626)唐高祖在亲祀太社诏中说:
四方之人,成勤殖艺,别其姓类,命为宗社,京邑庶士,台省群官,里闹相从,共遵社法,以时供祀,各申祈报,具立节文,明为典制。
表明了高祖皇帝对“别其姓类”的宗社的支持态度。到了高宗咸亨五年(674)曾经一度下诏
春秋二社,本以祈农。比闻除此之外,别立当宗及邑义诸色等社,远集人众,别有聚敛,递相承纠,良有征求。虽於吉凶之家,小有裨助,在于百姓,非无劳扰,自今以后,宜令官司禁断。
这是对于那些以结社为名,实则“别有聚敛”、“良有征求”行为及其组织的取缔,并非对所有的民间社邑实行禁止。实际上民间的私社也并未完全禁断,唐开元初年“同州界有数百家,为东西普贤邑社,造普贤菩萨像,而每日设斋”。这个每日设斋的普贤社在同州,距都城长安甚近,也可说明私社在民间的普遍存在。天宝元年(742)十月九日玄宗所下敕文中就说:“其百姓私社,亦宜与官社同日致祭,所由检校。”。这是说的官府在祭祀春、秋二社时,也让民间的私社也跟随同时祭祀。天宝七载玄宗所下的赦文中又说:
自今以后,天下每月十斋日,不得辄有宰杀,又闾阎之间,例有私社,皆杀生命以资宴集。仁者之心,有所不忍,亦宜禁断。
这是令民间私社在宴集时,不要杀生,同样也证明了私社在全国范围内的普遍存在。可见,民间的社邑一直存在着,并受到当局的支持和指导。
此处还值得一提的是,社邑有时还具有协助官府征收科税的功能。如S.2041《唐大中年间(公元847—860年)儒风坊西巷社社条》中的旧条部分载:
右上件村邻等众,就翟玉英家结义相和,赈济急难,用防凶变,已后或有诟歌难尽,满说异论,不存尊卑。科税之艰,并须齐赴。巳年二月十二日为定,不许改张。
篇2
——————————————————
①参见郑炳林:《晚唐五代敦煌地区种植棉花研究》,《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3期,第83—95页;《敦煌西域出土回鹘文文献所载qunbu与汉文文献所见官布研究》,郑炳林主编:《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续编》,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81—394页。
②参见刘进宝:《唐五代敦煌棉花种植研究——兼论棉花从西域传人内地的问题》,《历史研究》2004年第6期,第27—40页。
归义军政权按土地面积征收的官布是棉布还是麻布褐布,是这一问题的关键。因为褐布有两种解释,一是毛织品,二是麻织品。刘进宝先生认为褐布也可以称官布的依据主要是P.4887《已卯年八月廿四日袁僧定弟亡纳赠历》的记载“阎苟儿官布昌褐内接三丈”。①这里有几个问题,一是官布和昌褐是不是一种东西,是从属关系还是并列关系;二是“内接”的含义是什么。内接,根据《说文解字》:“接,交也。从手妾声。”段玉裁注曰:“交者,交胫也,引申为凡相接之称。”②将两件东西相交连接在一起就是接,除此之外没有第二种含义。“内接”,就是从里面(反面)将它们接在一起。接在这里既有动词的含义也有名词“接缝”的含义。如同卷文书记载有:“何社官:谈(淡)青褐又内接白斜褐内接长三丈”,意思是说把淡青褐与白斜褐从里边缝起来共三丈长。淡青和白色这两种颜色不同的褐不可能是一块褐布,因此官布和昌褐也不可能是从属关系,不是指官布中的昌褐,而是指官布和昌褐从里边接起来。纳赠历中凡是记载物品带有接者都是指两件或者两件以上交接起来的,如P.4975《辛未年三月八日沈家纳赠历》记载纳赠的丝织品带内接很多,一种丝织品有带内接者也有不带内接者,但是凡是两种丝织品放在一起者必须带内接字样,因为文书很长,引用起来比较麻烦,但记载到内接地方很多,很能说明问题:
1.辛未年三月八日,沈家纳赠历。
2.阎社长:绯绵绫内妾二丈三尺,又非绵绫内妾二丈五尺;紫绵绫内妾一丈三尺,又紫绵绫二丈;绿绢内妾一丈四尺。
3.窦社官:白绵绫古破内妾一丈一尺,绿绫子内妾一丈八尺,非绵绫内妾一丈五尺,又非绵绫八尺,黄绢、紫绵绫内妾一丈,古破白绵绫六尺,白绫六尺,白绵绫一丈九尺。
4.邓都衙:紫绵绫一丈八尺,白绵绫二丈四尺,非绵绫二丈,生绢一匹。
5.张录事:碧绸内妾二丈一尺,非绵绫内妾八尺,黄画被柒尺,紫绵绫内妾二丈三尺,非绵绫白绵绫内妾八尺。
6.邓县令:生绢一匹,白绵绫二丈六尺,又白绵绫一丈一尺;非绵绫二丈。
7.索押衙:白绵绫二丈八尺,又白绵绫二丈五尺,又白绵绫内妾、绿绢内妾二丈,生绢一匹。
8.阴押衙:小绫子一匹,索绫子一丈一尺,非绵绫、紫绵绫内妾一丈三尺,非绵绫二丈。
9.小阴押牙:黄绫子八尺,白绵绫一丈,非绵绫内妾一丈八尺,白绵绫一丈三尺内妾,又古破白绵绫一丈,白绵绫一丈一尺。
10.米押衙:白绵二丈四尺,紫绵绫内妾二丈三尺,白绵绫一丈三尺,楼绫一匹。
11.齐法律:非绵绫内妾一丈八尺,白绵绫一丈九尺,黄绫子、紫绵绫内妾一丈二尺,炎绵绫一丈九尺,白绵绫二丈。
12.邓兵马使:黄画被子七尺,白绵绫一丈,又白绵绫二丈,白绵绫二丈一尺,碧绸内妾一丈五尺,又碧绸六尺,又白绵绫二丈五尺。
13.邓南山:白绵绫内妾一丈八尺,非绵绫内妾一丈五尺,又非绵绫内妾紫绵绫三丈四尺,白绵绫二丈,又白绵绫一丈八尺。
14.杨残奴:紫绵绫二丈五尺,又紫绫一丈八尺,非绵绫七尺,又非绵绫一丈七尺,碧师内妾二丈六尺,又白绵绫二丈。
15.李愿盈:楼绫半匹,白绵绫一丈八尺,碧绢、白绵绫内妾二丈六尺,又白绵绫一丈五尺。
16.长千
(后缺)①
————————————
①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1辑,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第364页。
②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十二篇上手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600页。
本件文书记载将“内接”全部记载成“内妾”,接与妾通,乃音同假借或者音同致误。同类丝织品有带内接的,也有不带内接的,但是凡是两种丝织品作为一个计量单元的都带内接字样。如窦社官名下的“黄绢、紫绵绫内妾一丈”、张录事名下的“非绵绫白绵绫内妾八尺”、阴押衙名下的“非绵绫、紫绵绫内妾一丈三尺”、齐法律名下的“黄绫子、紫绵绫内妾一丈二尺”、李愿盈名下的“碧绢、白绵绫内妾二丈六尺”,黄绢与紫绵绫、碧绢与白绵绫不是一个品种,绯绵绫与白绵绫、非绵绫与紫绵绫、黄绫子与紫绵绫不是一种颜色,必须有接缝。一般不好理解的是将内接放在句后,另外两笔账就很容易理解:索押衙名下“又白绵绫内妾、绿绢内妾二丈”,邓南山名下“又非绵绫内妾紫绵绫三丈四尺”,前者衍一“内接”,这两条很容易理解成将两种丝织品缝接起来。就是刘进宝先生所引用的P.4887《己卯年八月廿四日袁僧定弟亡纳赠历》就有同样的记载:“谈青褐又内接白斜褐内接长三丈”,只是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而已。
接,不能理解成节或者段。敦煌文书S.1845《丙子年四月十七日祝定德阿婆身故纳赠历》记载该社纳赠的各种褐布45段,其中“碧褐白斜褐内接二丈二”仅算两段,段为个体计量单位而不是长度计量单位。段,从这件文书看,一段最短7尺,最长达35尺,无一定标准。②接,在很多情况下表示接缝,前引P.4887《己卯年八月廿四日袁僧定弟亡纳赠历》记载:“侯定残:白昌出斜褐内壹接壹丈,斜褐壹丈二尺。”壹接,就表示一个接缝。P.2842《乙酉年正月廿九日子L来儿身故纳赠历》记载:“武社官生褐三丈八尺,非(绯)褐内接二丈九尺”,“罗英达非(绯)褐内三接丈尺”。③前者表示红色的褐布里边有一个接缝,后者说红色褐布里边有三个接缝。S.2472《辛巳年营指挥葬巷社纳赠历》记载孔幸子“故烂半幅碧绢生绢内三接计丈五”,高员佑“帛练紫绵绫内两接一丈六尺”,④表示前者三个接口,后者两个接口。S.4472《辛酉年十一月廿日张友子新妇身故聚赠历》记载安再恩“紫褐、非斜内一接一丈付杜善儿”,梁庆住“紫粗褐、白斜褐内一接二丈”,王丑子“非褐、白褐裙段内四接二丈二”,马再定“白粗褐内一接二丈二尺”,李粉定“白褐、非绫褐、碧褐内接三段二丈”,王友子“立机二丈碧褐七尺故破内一接”,王残子“细紫褐七尺、非粗褐丈三内一接”,张清儿“白细褐、又非粗褐内两接三段三丈”。⑤从这些记载段和接区别很清楚,接就是接缝,两种褐布连接最少有一个接缝,三段连接必须有两个接缝。另外S.5509《甲申年二月十七日王万定男身亡纳赠历》记载社长韩友松“碧绵绫内四妾五段故破一丈二尺”、录事张通盈“黄绢壹匹白练故破内四妾五段”就更好理解,⑥五段丝织品缝接在一起有四个接缝。
通过以上分析,内接就是从里边缝接,作为名词就是指接缝,作为动词就是缝接。既然官布与昌褐作为一件需要缝接,那么官布与昌褐之间不是从属关系,而是并列关系。不是指昌褐中也有官布,而表明官布就是官布,昌褐就是昌褐,是两种不同的东西。刘进宝先生的官布昌褐“阎苟儿纳赠的是官布,其质地为昌褐,显然是毛织品无疑”的论断,有失偏颇。
————————————————
①《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1辑,第363页。
②《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1辑,第366—369页。
③《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1辑,第362页。
④《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1辑,第373—374页。
⑤《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1辑,第375—376页。
⑥《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1辑,第377—378页。
官布质地是棉布还是其他。刘进宝先生根据《晋书·刘隗传》、《南齐书·王敬则传》认为官布是上缴官府之布,即入官之布,既可以指麻布,也可以指棉布、毛布。晚唐五代敦煌地区官布的含义显然与中原地区不同,显然刘进宝先生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首先,敦煌地区的官布是否单纯是上缴官府之布或者入官之布。不可否认晚唐五代归义军政权按土地面积征收的官布具有上缴官府之布(入官之布)的性质,相当于唐代调布,问题是晚唐五代敦煌地区的官布有没有质地含义。唐代的赋税政策是随乡所出任土所宜,作为归义军政权一旦将官布征收对象固定化,就赋予了官布本身以质地性质。如果官布仅仅指入官之布,没有特指对象和质地含义,那么就不会在官府之外或者拥有者发生变化时还使用其官布名称。通过对敦煌文书分析研究,可知晚唐五代敦煌地区的官布除了按地征收之外,官布还作为商品在寺院民间大量流通,如P.3234《壬寅年(942)正月一日已后净土寺直岁沙弥愿通手上诸色入历》记载净土寺为张万川车头、索家小娘子念诵收入官布各一匹,①P.2032《后晋时代净土寺诸色入破历算会稿》记载净土寺为连兴押衙患病时诵经收入官布一匹立机一匹、为王都头车头念诵收入官布一匹,又为润子收新妇、莲台寺起钟楼各支付官布一匹。②官布作为念诵经价支付给寺院,或者寺院将官布作为礼品送给其他寺院个人,都是寺院与私人之间的商品流通,与官府无涉,特别是P.2846《甲寅年(945)都僧政愿清交割讲下所施麦粟麻豆等破除见在历》记载的收入布匹有土布和官緤,③官緤就是棉布,即官布和緤布。既然寺院将官布与緤放在一类,就表明官布与緤都属于棉布,是棉布中的一个品种。晚唐五代敦煌地区商品贸易中官布往往用作支付物价,北京图书馆殷字41号记载张修造西州充使曾于押衙王通通、押衙贾延德面上分别雇佣骆驼一匹,雇价分别为官布十六匹、官布拾个。④官布的来源和支付对象都与官府没有关系,之所以用官布支付驼价,这与西州贸易所得有很大关系。通过以上资料可知,官布不仅仅为向官府缴纳的布,就是在民间商业贸易别是寺院与寺院、寺院与个人、个人与个人间都用官布支付物价,因此官布已经突破了单纯的入官之布性质,成为当时布匹的一个品种。
其次,关于官布的质地是棉布还是其他,经过对敦煌籍帐类文书分析,官布与緤属于同种类别,都是棉布。前引P.2032《后晋时代净土寺诸色人破历算会稿》记载有緤破类总共九匹225尺,其中八匹就是官布。⑤P.2040《后晋时期净土寺诸色入破历算会稿》记载縹破类的51匹官布、各类緤共“緤计一仟一百七十五尺”,其中官布为23匹.⑥P.3763《年代不明(十世纪中期)净土寺诸色入破历算会稿》记载緤入类有“计緤八百一十三尺”,其中官布十七匹一丈七尺。⑦只有緤入緤破类有官布,其他类如布(土布)、褐类都没有记载有官布,表明官布与緤属于同一质地的棉布。最能说明问题的是P.3234《年代不明(十世纪中期)诸色入破历算会稿》,在布破类将“官布一匹乾元寺写钟人事用”,发现入错类后马上划去,又记入緤破类,⑧说明官布不是麻布而是緤布。
①《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3辑,北京:全国图书馆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第440页。
②《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3辑,第455—513页。
③《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3辑,第525页。
④北图殷字41号《癸未年四月十五日张修造雇父驼契》,《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2辑,北京:全国图书馆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第38页。
⑤《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3辑,第472页。
⑥《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3辑,第407页。
⑦《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3辑,第513页。
⑧《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3辑,第443页。
敦煌文书中保留的大量的支出账中有緤入、緤破类别,又有布入、布破类别及褐入、褐破类别,这里緤、布、褐含义是指什么,笔者认为緤指棉布,布(土布)指麻布,褐指毛织品。关于褐布指毛织品这一点,刘进宝先生也没有异议,布(土布)到底指什么,刘进宝先生论文没有涉及,作为麻织品没有异议,问题的关键是繅的质地是指棉布还是毛织品。刘进宝先生认为吐鲁番文书记载的西州地区的繅是指棉布,而将相邻的敦煌地区使用的繅布判定为毛织品,显然使用了不同的标准,另外敦煌地区从西州地区贩运来了大量的棉布,有安西繅、西州布等称谓,这里的安西緤是棉布还是毛织品,如果是棉布的话就在敦煌地区出现了出产于西州地区棉织品的緤和出产于敦煌地区毛织品的緤,为什么在敦煌籍帐类文献中没有将把安西緤和西州布放在褐类而加以区别呢,这就表明晚唐五代敦煌地区作为棉织品的緤与作为毛织品的褐有严格的区别。
晚唐五代敦煌地区从西州地区贩运了大量的緤布到敦煌市场上出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借贷文书记载出使西州前借贷的物品主要是丝绸,西州归来还贷的物品主要是緤,表明他们贩运回来的物品就是繅。这一点笔者在《晚唐五代敦煌地区种植棉花研究》第二部分“晚唐五代敦煌地区棉布的来源与产地”引用大量文书加以论述,如就弘子、张修造、贾彦昌、龙钵略、僧法宝、武达儿等西州充使回来后归还的本利都是緤,①证实了緤是从西州贩往敦煌的主要产品,这些緤布肯定是棉布无疑。二是晚唐五代敦煌地区有了经营西州緤的商贾。P.3156《庚寅年(930或990)十月已后破緤数》记:
庚寅年十月一日已后住儿西州到来破粗緤数:官家土物安西緤一匹、粗緤一匹,瓜州家棋价粗[緤匹]。官家骆驼价粗緤一匹,东河北头刺价与孔目细緤一匹,粗緤一匹。贴绫价细緤二匹,粗緤六匹。肃州去细緤六匹,粗緤十一匹。子弟粗緤一匹。音声粗緤一匹。高家粗緤一匹。宋郎粗緤一匹。②住儿无疑是从事西州棉布生意的商贾。文书中记载他经营的緤无疑是棉布。既然晚唐五代敦煌地区将西州地区出产的緤与敦煌地区出产的緤没有严加区分,证明二者质地没有本质区别。
篇3
Confuci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Entertainment
Culture in Medieval Dunhuang
CONG Zhen1 LI Chongshen2
(1 Research Institute of Dunhuang Studies,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20;
2. Institute of Silk Road Literature and Culture, Lan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Lanzhou, Gansu 730050)
Abstract: By interpreting the materials about entertainment recorded in the Dunhuang documents from the Library Cave,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entertainment culture was strongly influenced by the Confucian theory of "ritualism" as proved by the hierarchies and paradigms revealed in these activities. Local people had to consider whether their behavior was in accordance with Confucian rites when trying to relax and entertain themselves. Limited by ritual guidelines and ethical morality, the entertainment activities reveal an almost total lack of vitality and passion.
Keywords: Dunhuang;Entertainment culture;Confucian feature;Interpretation
游艺,顾名思义,就是游戏的艺术,是各种娱乐活动的总称,是人们以娱怀取乐、消闲遣兴为主要目的的一种精神文化活动。中国古代游艺活动深受儒家传统思想的影响,从本质上说,它没有独立的地位,而是依附于岁时节日、勾栏瓦肆、集会宴饮等活动中,并且始终受到礼的制约,以礼为本。敦煌莫高窟壁画和藏经洞出土文献中记载有较为丰富和相对完备的游艺活动资料,通过对这些资料的研读,发现其同样带有鲜明的儒家思想特征。这种特征在敦煌游艺活动中表现为活动程式的规范性、活动功能的象征性以及活动内涵的人文性。对这些特征的理解,有助于对古代敦煌人民的游艺生活面貌进行儒家精神层面的解读。
一 儒家经典对游艺的阐释
中国历代儒家经典著作中,有较多内容涉及对游艺的阐释,通过这些阐释可以比较清晰地把握所谓的儒家正统对游艺的认识。“游艺”一词,最早见于《论语·述而》:“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1]《说文》把“游”引申为“出游、嬉游。俗作遊。”[2]朱熹《四书集注》云:“游者,适情之谓。”[3]“艺”字,据何晏《论语集解注》解释为“礼、乐、射、御、书、数六艺。”[4]朱熹进一步解释为:“艺则礼乐之文,射御书数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不可阙者也。”[3]107对于游艺在儒家思想中的地位,朱熹曾论证道:“志道,则心存于正而不他;据德,则道得于心而不失;依仁,则德行常用而物欲不行;游艺,则小物不遗而动息有养。”[3]107清人周象明亦云:“格物谓穷乎物之理,游艺谓玩适乎艺之事,穷极其理讲学之先务,玩适其事德盛之余功,二者有初学成德之分。盖此是德盛仁熟之后,等闲玩戏之中,无非滋心养德之助,如孔子钓弋是也,从心所欲不逾矩,乃其境界欤!”[5]由此可见,在儒家的传统观念中游艺是以道德仁义为优先,亦即只有等到德盛仁熟之后,才能从事等闲玩戏的游艺活动。
正是基于上述儒家正统对游艺的阐释,致使历朝历代的封建大儒们对游艺活动进行了不同程度的限制,但事实上,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中,游艺作为人们休闲娱乐的重要内容,是无论如何也控制不住的。游艺活动不仅受到统治者的垂青,而且在民间也相当普及,成为中国人经常而又普遍的生活要素之一。因此,中国古代游艺活动的发展呈现出非常有趣的现象,一方面是正统思想的压制或不提倡,另一方面却是统治阶级、平民百姓甚至是儒家知识分子本身的身体力行。这使得游艺活动中人们既想放松身心、尽情娱乐,又不得不时刻考虑自己的行为是否合乎礼的规范,从而导致了游艺的双重属性和自身矛盾性。
二 敦煌游艺中所蕴含的儒家思想特征
篇4
中图分类号:K87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7)01-0020-01
这次敦煌学研究动态暨《敦煌研究》发展研讨会,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活动。及时把握敦煌学研究动态,引领敦煌学走向,是《敦煌研究》作为一个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期刊的重要任务。
依个人理解,近十多年来的敦煌学研究,大致出现了以下几方面新的趋向:(一)敦煌学研究外延的扩大,过去学者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献及敦煌石窟,现在,将敦煌出土汉简纳入敦煌学研究的视野,已逐渐成为学界共识。(二)随着收藏于世界各地的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献的公布,在百年敦煌文献整理的基础上,出版定本敦煌文献全集成为可能,必将为敦煌学界利用敦煌文献进行学术研究提供极大的便利。(三)敦煌石窟的研究方面,随着《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的出版发行,首次开启以考古报告记录敦煌石窟的新时代,标志着敦煌石窟考古报告工作全面开展。与此同时,敦煌石窟的研究开始进入探索石窟内容所反映的佛教思想、流派、信仰和社会、历史问题,以及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等深层次问题的研究,与敦煌石窟相关联的中外文化交流的研究、敦煌文献与敦煌石窟相结合的研究也成为主敦煌石窟研究的新趋向。(四)敦煌学研究由微观走向宏观,由分析走向综合,利用交叉科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成为敦煌学新的亮点。(五)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以敦煌为中心,西域、中亚等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或地区与敦煌的文化交流再度成为敦煌学关注的新动向。前面s新江先生关于《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研究动态》的发言,就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启示。(五)敦煌学学术史研究开始受到重视。(六)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为敦煌学研究提供了科技支撑。
《敦煌研究》是敦煌学研究领域享有盛誉的学术刊物,也是敦煌学研究领域无可代替的学术刊物,多年来,《敦煌研究》以其鲜明的办刊特色和高水平的学术论文,赢得了国际敦煌学界的认可。关于《敦煌研究》未来的发展,我个人认为,首先要继续保持《敦煌研究》的独特风格,这是《敦煌研究》期刊立足于学术期刊之林,并获得学术地位的关键所在。其次,立足敦煌,面向世界,以开放包容的精神,刊发国内外敦煌学及相关学科研究的新成果、新资料、新信息,推进敦煌学研究的国际化。第三,根据敦煌学研究的新动态,《敦煌研究》期刊要发挥引领学术发展导向的作用,特别是《敦煌研究》多年坚持设置专栏,组织专家学者参与撰文讨论,引导学术的做法,值得继续发扬。第四,培养作者队伍,刊发高水平学术论文。第五,加大投入,做好《敦煌研究》网站的编辑及期刊论文数字化工作。
篇5
《远东亚洲丛刊》(Cahiers d'Extrême-Asie)是法国远东学院京都分部的法文、双语刊物。1985年创刊,第一任主编索安(Anna Seidel)女士是一位道教史专家。它是一种年刊,但有时两年合出一卷,譬如我们要介绍的11卷就是如此。每卷篇幅约三、四百页,刊出十余篇论文,印数为1000册。编委会成员以远东学院研究人员为主,也邀请一些院外的法国学者。刊物特色为东亚宗教史、社会史和文化史,尤其注重从人类学角度考察宗教现象的研究成果。经过几年的努力,该刊已经成为国际汉学界的极具特色的领首刊物,影响力绝不低于已有百年传统的《法国远东学院学报》。
翻开卷首,是本卷特邀主编戴仁(Jean-Pierre Drège)用法文和英文撰写的《致读者》。戴仁是法国当代汉学界的主将。他是苏远鸣(Michel Soymié)的弟子,法国远东学院的资深研究者。八十年代后,他进入法国高等研究实验学院,1989年被任命为“中国图书与铭文史”研究导师,并曾担任敦煌写本研究组的主任、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所长。从1998年起出任法国远东学院院长。戴仁以利用敦煌文献研究“书籍考古学”而著称,与已故的日本著名敦煌学家藤枝晃一样,在敦煌文献的物质形态研究领域卓有建树。戴仁的研究涉及到了中国古代书籍的具体制作的所有细节,并试图阐述它们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包括纸张的纤维、装帧、文字分析、印刷术、写本和刻本的断代与辨伪、图书馆学、书籍的插图及其与行文的关系、书籍的发行流通、书籍商品化的过程及其文化和社会意义等等。其代表作为《中国写本的藏书》(参看荣新江书评,《九州学刊》第六卷第四期,收入《鸣沙集》),另著有相关论文数十篇,还出版过几部有关丝绸之路的著作,其中一部已被翻译中文。此外,他还主编过多部敦煌学和书籍史、印刷史的论文集。
戴仁在这篇卷首语中指出,一百年前王圆籙的意外发现,产生了惊人的后果,那就是促使我们对有关中古时代中国原有知识的一切领域进行彻底重估,这一重估已体现在了的汗牛充栋的论著中。接着,他简略地回顾了近三十年来法国出版的几部重要的敦煌学论文集。然后分别用寥寥数语但却画龙点睛般地对本专辑所发表的每篇论文作了评介。
苏远鸣《敦煌画中的供养人》
苏远鸣和谢和耐一样,是师出“法国二十世纪下半叶的汉学大师戴密微”(见谢和耐同题文章,《法国当代中国学》,戴仁主编,耿昇译,中华书局,1998年,119-133页)的得意门生,是当下法国敦煌学界的元老级人物。他也是法国远东学院的资深研究者,曾任法国高等研究实验学院“中国中古及近代史学与文献学”研究导师达二十余年之久。他是《敦煌学论文集》第1、2、3卷的主编,并主持了《法国国家图书馆藏伯希和敦煌汉文写本目录》第3、4、5卷和两卷本的《法国国立吉美艺术博物馆藏伯希和收集品》这两个大项目的编撰工作。除了对敦煌文书的释读、编目、字体演变和断代以及敦煌绘画深有研究之外,苏远鸣还致力于中国道教和佛教互动关系的研究,如佛教疑伪经和道教文献的比较研究,佛教仪式与道教仪轨之间的对比分析等,开辟出许多新的学术领地。他的学术兴趣甚广,还涉猎宗教地理研究、中国解梦书研究、河西宝卷和明清小说的类型学研究等等。
苏远鸣六十年代即开始运用图像学和敦煌写本研究结合的范式探讨地藏菩萨诸弟子,敦煌壁画中的瑞像图,明王和金刚,壁画和纸画、绢画、幡幢上的题记等。因此本文可看作他系列研究的新尝试。他使用了敦煌莫高窟北凉时期的275窟、西魏时期的285窟以及数十幅收藏在大英博物馆的斯坦因收集品和法国国立吉美艺术博物馆的伯希和收集品中的纸画和绢画,从八个方面考察了敦煌石窟中的供养人像:1、资助绘制壁画的目的;2、家族世系;3、新婚夫妇;4、香炉;5、僧尼;6、亡人;7、服饰和头饰;8、画匠。苏远鸣认为之所以要绘制这些壁画,是为了敬献给亡灵,而不是生者为了祈求保佑。
敦煌壁画中的供养人像的研究成果虽然不像经变图、佛传、本生故事图、瑞像图、生产生活图那样丰富,但由于它在考证石窟修造年代和河西史实方面具有重要的参照价值,因此很早就受到学者们的重视。王国维先生早在1919年所作的《于阗公主供养地藏菩萨画像跋》(《观堂集林》卷二十,中华书局,1959年重印本,999-1001页)是这一领域的开创性论著。八十年代,国内出过一本有用的资料集——《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敦煌研究院编,文物出版社,1986年),附收了万庚育的《珍贵的历史资料——莫高窟供养人画像题记》(179-193页)、贺世哲的《从供养人题记看莫高窟部分洞窟的营造年代》(194-236页)两篇论文。相关的研究成果还有关友惠《敦煌壁画中的供养人画像》(《敦煌研究》,1989年第3期)、段文杰《供养人画像与石窟》(《敦煌研究》,1995年第3期)等,但大多比较简略,而且讨论的对象仅限于壁画中的供养人像。因此正如戴仁所言,这一课题虽然不是很新鲜,但本文的研究非常“系统而清晰”(本书《卷首语》)。
篇6
本文的简略回顾表明,数十年来,我国学者在这一方面已做了许多重要准备工作。如对归义军政治史的研究、对敦煌历史地理的研究等都已经相当深入,并有总结性论著问世。有的相关类别文书如碑铭赞类文书和契券文书的整理和研究也已达到较高水平。但仍有许多方面需要加强,不少方面有待展开。如归义军时期的经济史、佛教史、社会史和文化史等方面都值得投入更多的力量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有些方面甚至需要较长时间的准备以后才能进行总结。如敦煌佛教史需要对相关文献进行系统整理和研究,完成“敦煌佛寺志”、“敦煌的佛教与社会”等系列专题研究以后,才有可能在这方面进行总结性研究。敦煌社会史也要在完成“敦煌氏族志”等系列专题研究后才有可能进行总结性研究。至于敦煌文化史,我们以前做的工作就更有限,大量的工作有待展开。可见,在本世纪的最后几年和下一个世纪,专题研究应进一步加强。因为只有在深入的专题研究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写出有分量的专史,而各方面专史的完成又是全面综合研究的必要准备工作。在从事专题研究过程中,需要完成大量艰苦的微观考察。不少工作表面看来十分细碎甚至繁琐,无关大局,如过去我们对归义军政治史许多小问题的探索就容易使人产生这样的印象,但这些微观探索又是我们全面、深入、系统地考察敦煌地区必不可少的工作。当我们将这些具体的探讨整合为对整个敦煌地区的微观透视时,就会发现在敦煌文献研究领域,微观考察的意义不同一般。
当然,要完成对敦煌地区的全方位考察,仅靠专题研究还远远不够。必须同时积极开展综合研究与宏观研究。在第一、二阶段,我国学者因受到资料的限制,往往只能就所见少量文书或一件文书进行阐发,研究是点式的,很难做专题或综合研究。到第三阶段,我们能见到的材料日益增多,对敦煌文献做分类整理或专题研究的学者也逐渐增多。但对各类文书、各个专题、各个学科进行的综合研究还很薄弱,将敦煌地区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的工作也有待展开。就目前而言,首先应注意从整体上把握敦煌文献。敦煌文献虽然分属各个学科,可以分为许多类别,但同时又是一个整体,各类文献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如人们利用有关10世纪的一大批文书研究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宗教和社会,已取得了很大成绩,若在此基础上将这一时期的各类文书打通,相信对这一时期整个社会的了解将更加全面,更加深入。其它如对历史资料与文学史资料等各学科之间联系的研究,汉文历史文献与藏文历史文献等各文种之间联系的研究,也都是具有很大潜力的研究领域。在下一个世纪,当各个专题和综合研究都达到较高水平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考虑撰写贯通中古时期敦煌政治、经济、社会、宗教、文化等领域的《敦煌中古史》了。
其二,敦煌文献为我们进一步研究9世纪中叶至11 世纪初西北地区的民族史提供了提供了大量原始资料。9世纪中叶至11世纪, 是我国西北地区民族发生大变动的时期。但传世史籍有关这方面的记载较少,很难据之进行深入系统的考察。敦煌文献中保存了一批反映这一时期民族情况的汉文、藏文、回鹘文、于阗文、粟特文公私文书,为我们探讨西北地区民族变迁、各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与相互间的交往提供了可能。本文的回顾表明,我国学者在利用这些资料方面已取得很大成绩。特别是第三阶段,我们不仅在利用敦煌汉文文献研究西北地区民族问题方面取得了不少成果,在对少数民族文字历史文献的整理和研究方面也有较大进步。同时应该承认,我们这方面的工作做得还很不够,与国外同行相比还存在不少差距。在少数民族文字文献研究方面,一些文种与国外的研究水平差距还比较大,取得的成果仍以第二次译释居多,能直接解读少数民族文字文书的学者亦嫌太少。所以今后应进一步加强对少数民族文字文书的整理和研究。特别是藏文文献,数量很大,值得投入更多的力量进行全面的整理和研究。另一方面,在研究西北地区民族问题时,应提倡在全面搜集各方面资料的基础上将敦煌汉文文献、各民族文种文献与传世文献融会贯通。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得出比较合乎实际的结论。以往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所以分歧较多,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一些研究者有时仅据部分材料就勿忙做出了结论。
其三,敦煌文献还为解决中国古代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提供了材料。古代的敦煌是中国的一个地区。所以,敦煌文献不仅对了解敦煌地区具有重要意义,其中的许多材料还反映了中原地区的一般情况。我国学者在利用这些材料方面也做了许多工作。如均田制即属中国古代史的重大问题,但在敦煌文献发现以前,对其实施情况的研究始终无法深入。我国学者主要依据对敦煌文献中有关材料的具体探讨,才为均田制实施与否的争论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并对均田制的实质形成了新的认识。又如本文所述我国学者对敦煌法律文书的持续探索,不仅解决了许多有关唐律和唐代历史的具体问题,还使学术界对久已亡佚的唐代令、格、式等法律文献的形式、内容、性质有了具体而形象的了解,并为令、格、式的辑佚提供了样式。再如本文所述我国学者对唐代勾官的研究,也是在具体探讨敦煌、吐鲁番文献中有关勾官进行勾检的记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对唐代勾官和勾检制度的整体认识。对敦煌文献中反映中原地区一般情况的材料作微观考察,容易使人产生细碎繁琐的感觉,但从中获得的知识不仅有助于认识同期中原地区的情况,有时对认识某一事物或社会现象在整个中国古代的发展脉络亦有助益。如前述我国学者对中国古代社邑发展情况的探讨和对中国古代书仪源流的考察,都在不同程度上借助了从相关敦煌文献研究中获得的认识。
我国学者在利用敦煌文献解决中国古代史上的问题方面虽然做了不少工作,但在这方面仍有许多工作有待完成。如有关佛教史和社会史方面的资料就利用得很不够。在今后的研究中应提倡将敦煌文献放到更大的背景下进行考察,在对敦煌文献和传世文献、石刻文字中的相关资料作彻底调查的基础上,将敦煌文献中有关某一专题的资料放到唐宋时期甚至中古时期的历史背景下进行考察。
其四,古代的敦煌是中国和世界接触的窗口。所以,敦煌文献中保存了不少反映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资料。我国学者利用这些资料探索中国与印度、中国与波斯等地的经济文化交流,探索丝绸之路的贸易等课题都取得了重要成果。但与敦煌文献中保存的这方面材料相比,还有许多工作可做。特别是在唐代,敦煌汇聚了中国、希腊、印度、中亚、西亚等不同系统的文化,这些在敦煌文献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站在中古时期世界文化交流的高度,全面系统地发掘敦煌文献中有关这方面的信息,将是21世纪的一项重大课题。
以上分析表明,我国学者在20世纪虽然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但尚未解决的问题和有待开展的工作更多。所以我们有必要认真总结过去的经验,力争在21世纪取得更大的成绩。回顾20世纪我国学者利用敦煌文献研究历史的历程,似有以下一些因素对研究的进展和研究水平的提高具有较大影响。
第一是资料的限制。对我国一般史学工作者而言,在前两个阶段能见到的敦煌文献数量有限。虽然在第二阶段我国已有英藏敦煌文献主体部分的缩微胶卷,由于种种原因,能直接利用的人很少。多数史学工作者了解、利用敦煌文献仍主要依靠少量很不完善的敦煌文献录校本。到第三阶段,我国学者终于可在国内看到英、法和北图所藏敦煌文献的主体部分。但有关敦煌文献的缩微胶卷和影印图集实际上只有少数高校和科研单位有条件购置,对多数史学工作者来说,查阅敦煌文献仍有诸多不便。另一方面,由于敦煌文献多为写本,其中保存了大量的唐宋时期的俗体字和异体字,还有不少写本使用河西方音。这就要求阅读某件文书的学者不仅要掌握该文书有关学科的专门知识,还应当对敦煌的历史、敦煌俗字及河西方音等整理敦煌文献所需的专门知识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否则,即使有条件直接查阅敦煌文献,在阅读过程中也会遇到重重困难。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使得拥有缩微胶卷和图集的单位,其资料使用率并不高,查阅者多为专门或主要研究敦煌文献的学者。一般史学工作者了解、利用敦煌文献仍主要依靠录校本。可见,资料方面的限制,一直是影响我国史学工作者了解、利用敦煌文献的重要原因。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应是21世纪的首要任务。因采用先进技术重排、精印敦煌文献图版是正确释录文字的前提,所以应在现有基础上加快敦煌文献图版的编辑、出版步伐,力争在下一世纪初叶完成这项工作。同时加快对敦煌文献的整理、录校工作,这既包括分类对敦煌文献进行录校,也包括按号对敦煌文献作全面录校。目前,分类录校正在有计划地进行,全面录校的工程也已启动。这项工作是将敦煌文献推向学术界的基础工程,是为史学工作者解除资料方面限制的关键步骤,希望能得到各方面的重视和支持,争取在下一世纪的前20年完成此项工作。当然,录校工作一定要保证质量。近年出版的一些录校本即因质量不佳受到学术界批评。
第二是史学观念的影响。在第一阶段前一时期,用传统方法治学的罗振玉等人对历史典籍和有关政治史的资料比较感兴趣。后一时期陶希圣利用《食货》出版《唐户籍簿丛辑》,显然是其社会史史观使然。第二阶段我国学者对社会经济资料关注较多,也明显受到用史观研究社会经济史风气的影响。在第三阶段,随着各种新的史学观念和新方法的流行,利用敦煌文献研究历史各方面问题得以全面展开,其中尤以社会史观念的重新流行影响最为显著。数十年的敦煌文献研究史表明,新的史学观念和新的研究方法有利于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地发掘敦煌文献的史料信息,应该大力提倡。
篇7
[9]郭朋.隋唐佛教[M].济南:齐鲁书社,1980:524.
[10]郭朋.坛经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2:9.
[11]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63:204.
[12]黄夏年.禅宗研究一百年[J].中国禅学: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2002[2012-12-10].http:///magzine/zgcx/zgcx146.htm.
[13]李淼.中国禅宗大全[M].长春:长春出版社,1991:776.
[14]潘重规.敦煌写本《六祖坛经》中的“獦獠”[J].中国文化,1993(9):165.
[15]饶宗颐.敦煌俗字研究导论·序[J].中国文化,1995(11):267.
[16]饶宗颐.慧能及《六祖坛经》的一些问题[C]//六祖慧能思想研究——“慧能与岭南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广州:学术研究杂志社,1997:234-235.
[17]张新民.敦煌写本《坛经》“獦獠”辞义新解[J].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3):88.
[18]蒙默.《坛经》中“獦獠”一词读法——与潘重规先生商榷[J].中国文化,1995(11):256-257.
[19]张新民.“獦獠作佛”公案与东山禅法南传──读敦煌写本《六祖坛经》札记[J].中华佛学学报,2003(总第16期):109-131.
篇8
敦煌遗书、汉晋简牍、安阳甲骨和大内档案被称为上个世纪初的四大发现,由此而兴起的敦煌学、简牍学、甲骨学等三大新兴学科成为世界性显学。
从1907年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时在敦煌、酒泉汉代边塞烽燧遗址掘获大量汉简以来,至今已整整100年了。100年来,全国各地发现的汉简有70多批(次),而甘肃就有30多批(次);全国各地共出土汉简7万余枚,而甘肃就有6万余枚,占全国出土汉简的82%左右。甘肃简牍内涵丰富,形制多样,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外交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具有极高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不仅属于甘肃人民,也属于整个中华民族和全人类。
1914年,我国著名学者罗振玉和王国维在日本发表了《流沙坠简》,成为中国简牍学的奠基之作。居延汉简出土后,劳干先生在抗战时期那种艰苦的环境中先后完成了《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居延汉简考释――考证之部》和《居延汉简考释――图版之部》,成为居延汉简研究的经典之作。1959年,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整理出版了《居延汉简甲乙编》、《武威汉简》等,其后陈梦家先生结集出版了《居延汉简缀述》,陈直先生结集出版了《居延汉简研究》。甘肃省学者先后出版了《汉简研究文集》、《秦汉简牍论文集》、《居延汉简通论》、《居延新简释粹》、《敦煌悬泉汉简释粹》、《甘肃考古文化丛书――简牍》等一批有份量的学术著作,还整理出版了《居延新简――甲渠候官》、《敦煌汉简》、《散见汉简合辑》等一批重要的原始资料。仅居延汉简的研究,已有90多部专著出版、880多篇,如果把全部甘肃简牍的研究成果加起来,论著接近200部,论文有数千篇,至于将简牍研究成果交叉渗透到其他学科而产生的新成果就更是难以计数。
几十年来,甘肃简牍的保护和研究一直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钱伟长、赵朴初、李铁映、张德勤、聂大江等同志就曾对甘肃简牍保护问题作过指示。特别是近几年来,甘肃简牍的保护研究,再度引起了甘肃省委、省政府的重视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国务委员陈至立同志作过重要批示,国家文物局领导曾多次来现场考察,省内文化界政协委员连续几年提出提案。作为主管部门的甘肃省文化厅和甘肃省文物局,更是每年都将落实工作列为重要的议事日程。
2007年10月18日,甘肃简牍保护研究中心成立揭牌。这是甘肃省文化建设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甘肃省建设特色文化大省的一项重要举措和全省文博事业取得的又一重要成就。甘肃简牍的保护研究,将以此为起点,跨上新台阶,做出新成绩,以崭新的面貌为甘肃的文化建设争得荣誉和地位。
篇9
“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三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于8月18—20日在首都师范大学举行。来自英、法、美、俄、日等国及中国大陆、台湾的130多位敦煌学研究者欢聚一堂,共同回顾30年来敦煌吐鲁番学研究的发展历程,深入探讨敦煌学的相关问题。本次学术研讨会由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敦煌研究院和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四家单位主办,北京大学东方研究院、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敦煌学研究中心、吐鲁番学研究院、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和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协办。承办单位是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还提供了赞助。
本次会议是近年来敦煌学研究领域规模最大的一次学术盛会,共收到论文100多篇。会议分两个小组,进行了19场共105个学术报告,研讨内容既有对敦煌吐鲁番学研究工作与成果的总结,也有对敦煌吐鲁番学前沿问题的关注,还有大量针对敦煌文献和石窟艺术的个案研究,内容涉及古代历史(包括法律、典章制度、社会民俗等)、文学、艺术、语言学、民族学、宗教学、古代科技(如医学、天文等)等领域的问题。开幕式上,老一辈学者(80岁以上者)冯其庸、金维诺、宁可、沙知、王克芬、唐耕耦、白化文、陈国灿等在主席台就坐。参会的学者既有中老年一大批知名学者,也有相当多的青年才俊,充分展示了当今国际敦煌吐鲁番学的研究水平和学术阵容。本次学术会上,敦煌研究院12位学者参加了会议,包括樊锦诗、马德、张先堂、赵声良、王惠民、杨富学、杨秀清、张元林、陈菊霞、张小刚、张景峰、赵晓星。他们分别发表了在敦煌石窟、敦煌文献等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尤其是一些年轻学者的论文,显示了新思路、新成果,引起了与会学者的关注。
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于1983年,正值改革开放、文化振兴的时代。中国学者们意气风发,努力钻研,极大地推动了敦煌吐鲁番学研究的发展,30年来,不仅在相关的各领域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果,而且在国内许多重点大学开设了敦煌吐鲁番学课程,有的学校还设立了敦煌学博士点,培养了大批青年敦煌学研究人才。30年间,国外收藏的敦煌学资料中最主要的部分如法、俄、英等国的文献都逐步由中国学者整理,并在中国系统刊布,而国内各单位收藏的敦煌文献也大部分整理出版。敦煌石窟方面也出版了《敦煌石窟艺术》、《敦煌石窟全集》等大型图录。与此同时,英国的IDP、法国国家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及敦煌研究院等单位通过网络建设,构成了极为便利的学术资源网站,这些工作极大地推动了敦煌学的全面发展。到21世纪初,中国敦煌吐鲁番学的发展已经在很多方面产生了集成性成果。近年,荣新江、柴剑虹先生主编的30多卷本《敦煌讲座》丛书(即将出版),正是中国敦煌学成果的集中体现,敦煌吐鲁番学越来越展现其勃勃生机。
篇10
一、敦煌社会信仰的研究概述
关于敦煌社会信仰的研究,日本学者研究起步较早且成果较多,如小田义久(1965年),游佐N(1981年),金文京(2000年)等对中古时期敦煌社会信仰均有比较深入的研究。那波利贞《唐代社会文化史研究》(创文社1974年)、金冈照光《敦煌の民――その生活と思想》(东京评论社1972年)等虽不是有关敦煌社会信仰的专著,但其论述中偶有涉及者对后人亦多有启发。对社会信仰问题,欧美诸学者的研究也很有见地,如英国王斯福《帝国的隐喻:中国民间宗教》(1992年),以中国东南地区民间宗教和信仰为例,对中国人日常生活及其信仰做了比较客观的考察;美国太史文《幽灵的节日:中国中世纪的信仰与生活》(1999年),以中国的鬼节为研究对象,比较深入的讨论了南北朝至唐代流行于上至帝王,下至庶民间的具有极其广泛性的宗教性活动,反映了唐代社会信仰的丰富性;韩森《变迁之神:南宋时期的民间信仰》(1999年),以民众对神o的选择为研究对象,重点讨论了南宋时期的民间信仰;韦思谛《中国大众宗教》(2006年),重审了“大众宗教”的概念,其所选论文分别就“晚期中国”大众宗教的某一方面进行了深入论述,同时,也提供某些可资借鉴的方法。国内关于唐宋时期敦煌社会信仰的研究,近年来逐渐兴起,成果颇丰,但其所涉及多为,特别是以佛教信仰居多。李正宇(2001年)、颜廷亮(2000年)、张先堂(2001年)、杨秀清(2003年)等诸位先生对敦煌的“世俗佛教”做了许多探索性的研究。其他学者虽无专文论述,但文中偶有涉及者亦不乏卓识高论。如卢向前(1992年)对民间神o的精辟论述,谭蝉雪(1993年)对民间祈赛对象及其祭品的研究,高国藩(1999年)以敦煌民俗为主要内容对当时敦煌民间信仰的探讨,段小强(2001年)对敦煌地区祖先崇拜仪式的探讨等。刘永明(2005年)重点探讨了敦煌世俗信众中的佛、道融合问题;余欣(2006年)从社会生活层面,探讨了唐宋之际民众的信仰世界;党燕妮(2009年)对晚唐五代宋初敦煌流行的各种佛教信仰进行了比较系统、深入的考察,进而考察了其特点及其社会功能。另外,黄正建(2001年)、郑炳林(2004年)、金身佳(2007年)、陈于柱(2007年)、王晶波(2010年)等学人分别从占卜、梦书、风水、算命及看相等视角为切入点,通过观察世俗信仰与当时诸宗教的互动关系、借以审视敦煌社会的信仰问题,这为探讨当敦煌社会信仰研究开出了一条重要的学术思路。
二、敦煌社会信仰的研究特征
敦煌地区独特的生态环境、地理环境及多元文化交汇的文化特点;一是敦煌地区唐宋时期历史发展的特点;一是在这种文化环境中,民众的价值观念、心理特征、行为方式的特点。而判断一个地区的文化主流,主要依据是考察这一地区支撑社会生活中信仰与价值取向的知识与思想,以及在文化传播与文明传承中影响文化发展方向的文化现象。
敦煌社会信仰是一种世俗信仰、混融信仰,各种信仰共纳融合,佛教信仰(如弥勒信仰、观音信仰、毗沙门信仰、药师信仰、维摩诘信仰等)、道教斋蘸与法术、山神川原(金鞍山神、张女郎神、玉女娘子等)及官方神主(社稷、风伯、雨师)等领域。尤其是发唐后期五代宋初归义军时期(848-1036),佛教信仰几乎成为了敦煌人“一般的知识与信仰”的主体部分,敦煌佛教空前兴盛并日益世俗化,民间佛教信仰成为敦煌佛教的主流,渗透到敦煌社会、经济、军事、文学、艺术、思想意识、婚丧嫁娶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信徒遍布社会各个阶层,形成了一个异常庞大的民间信仰群体,这些信仰广泛地影响着当时敦煌民众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敦煌社会信仰以对现世幸福的追寻为最终归宿,其核心信念是因果报应和功德思想。敦煌社会信仰不需要高深理论的指导,而是以简单、直观、实用的原则为基础。敦煌社会信仰渗透于敦煌民众日常社会生活之中,并表现出类型化或模型化的特征。敦煌社会信仰既是一种意识形态、又是一种实用技术,既给人以精神上的信念、又提供一些心理上的工具。在日常生活中对民众产生影响的知识、技术与思想,则上升为与主流价值判断和道德标准相一致的大众文化,担负起传播知识和教育大众的职能,和精英文化的大众化相比,在敦煌文化区中,后者对敦煌地区的社会生活的影响要更大一些。
三、敦煌社会信仰观念的传播途径
敦煌社会长久以来形成的习俗、规则、各类文化娱乐活动及生活经验对民众潜移默化的影响,如演戏、说书等,常常把最通俗、最简单化的思想与信仰观念传达给大众。各种日常法事活动、民俗化的宗教节庆及传统仪式的暗示,如诵经、说法、礼忏、祭祀、婚丧仪式等;晚唐五代时期在敦煌大众社会生活中流行的“障车”、“下婿”、“去扇诗”等婚姻礼俗,是如何被写入当地士大夫家族亦行用的《今时礼书本》和《下女夫词》中,我们就不难发现这一事实。按照文化社会学的有关理论,根据敦煌地区的历史文化特质,可以把唐宋时期的敦煌地区作为一个特定的文化区来考察。世俗信众的各种功德活动对民众的影响,如写经、开窟、燃灯、布施等。各类启蒙读物及通俗读物在民间的广泛传播,如蒙书、俗文学、选本、善书以及口头文、书仪、类书、具注历等。按照传统思想史中的描述来考察唐宋时期敦煌地区的社会生活,我们发现,在实际生活中,影响大众信仰与行为取向的知识与思想,和我们过去思想史研究中的叙述与解释还有一定的距离,而敦煌文献及敦煌石窟的有关内容,系统而又真实地反映了唐宋时期敦煌大众的知识与思想,这是其他史料无法与之相提并论的。普及性教育中直接或间接地指示,如私学、寺学、父母与亲友的教导及对经典的世俗化演绎等。
四、敦煌社会信仰传递的知识与思想
唐宋时期敦煌社会信仰的观念几乎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每个侧面、每个层次,其所构建的虚幻世界与真实的社会生活平行的存在,并深刻影响着当时民众的衣食起居、社会生活乃至精神与思想。信仰观念潜移默化的熏陶和其传播途径的宣传,使唐宋时期敦煌社会信仰传递的知识与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日常生活的规则,如禁忌与行为规则、卜兆与人生轨迹的选择、行祭施禳等。
2、社会生活的观念与社会生活的规范,如社交心得、为人处事的原则、社会生活的经验等。
3、基本的道德构成与伦理秩序,如基本的礼仪知识、孝养思想等。
4、关于人生幸福的思想,如个人、家庭、家族的平安、丰衣足食乃至兴旺发达、子孙繁衍等传统观念。
5、关于免祸消灾、解难除厄、追求福报的思想。
敦煌社会信仰是全社会的和全体民众的创造,它不是个人有意无意的创造,敦煌社会信仰与社会生活及生活中的民众密切相关,它的存在,不是个性的,大都是类型的或模型的。敦煌社会信仰在时间上具有传承性,在空间上具有扩布性;在地域上具有特殊性,因此,我们在研究中应该注意主流文化的地域性特征。
以上大致回顾了有关社会信仰及敦煌信仰的研究成果,只是择其要者进行了粗略地列举和简评,这些研究主要是对敦煌佛教信仰及民间信仰等方面粗线条的勾勒和概括。唐宋时期敦煌民众的信仰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情景,当时社会大众普遍信仰并接受的知识和思想究竟是怎样的以及这些知识和思想是如何影响当时人们的价值观念、行为取向的等问题至今仍未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轮廓。因此,“敦煌研究必须从文献研究转向历史学研究”,从社会史的角度,通过对唐宋时期敦煌社会信仰的全景式考察,探讨影响当时整个社会的知识与思想,以及这些知识与思想对当时人们价值观念、行为取向的影响。
主要参考文献
1.敦煌社会信仰类文献
(1)金照光.敦煌の民――その生活と思想[M].东京:评论社,1972.
(2)游佐N.敦煌文献ょり见た唐五代にぉける民间信仰の一侧面[J].东方宗教,1981,(57).
(3)高国藩.敦煌俗文化学[M].上海三联出版社,1999.
(4)颜廷亮.敦煌文化[M].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
(5)黄正建.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研究[M].学苑出版社,2001.
(6)李正宇.唐宋时期的敦煌佛教[J].//敦煌佛教艺术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M].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368.
(7)杨秀清.唐宋敦煌地区的世俗佛教信仰――以知识与思想为中心[J].//项楚,郑阿财.新世纪敦煌学论集[M].巴楚书社,2003.
篇11
在以iphone为代表的智能手机当道的现代社会中,手机配件市场异军突起。作为商品手机本身更换个性颜色和款式的界面幅度不大,但手机配件可根据个人喜好随意改变,因此备受用户欢迎。但目前市场的手机保护套与其他配件设计元素极其缺乏典型文化艺术标识,这种设计模式极易随着社会泡沫式的浪潮昙花一现。因此树立具有文化艺术与商品融合的个性标识是有着现代商品设计发展的必要性。
随着敦煌壁画元素产业的飞速发展和进步,与敦煌壁画元素相关的衍生产品系列也开始走红市场。而“敦煌壁画元素传统文化”逐渐被消费。人们常说的“敦煌壁画元素传统文化”其实是用于现实穿着并通过市场开发得以实现最终盈利的“敦煌壁画元素衍生的传统文化产品”,它是敦煌壁画元素的现实呈现和商业价值体现的重要载体。在我国,敦煌壁画元素衍生产品的开发、生产企业少之又少,市场流通产品很难找到一个有力恰当的切入点。
在研究国内外优秀敦煌壁画元素的基础上,分析的传统艺术元素在手机配件领域的设计关系极其对手机配件商品社会经济效益所产生的影响。在对敦煌壁画元素造型设计的过程中,手机配件领域的设计与传统文化是鱼与水的关系:它离不开传统文化造型;传统文化造型也不是独立的个体,它要以手机配件领域的设计为载体依据,要体现造型特点,深化产品性格。
以敦煌壁画中传统飞天元素的现实化与当代化是弘扬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手段,敦煌飞天所蕴含的平面设计色彩与构成元素对手机配件及其产业链有重要影响。现在随着智能手机的畅销,手机配件有很大的潜在市场,但目前市场较混乱,没有一个主导品牌。所以研究开发带有敦煌壁画艺术的手机保护壳及衍生品其对手机配件市场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敦煌壁画中的色彩搭配及构成对中国元素手机配件的设可参考的理论与经验,敦煌壁画元素在手机保护壳上的一些简单运用,抽象又不失现代风范。表达传统文化的同时又可以充分彰显自己的性格
以敦煌艺术为符号的商品目前仍停留在低层次水平,旅游品市场无序竞争,低端艺术品价格虚高。长此以往,敦煌艺术难以发展;要适应市场做产业化,就必须整合当地资源,找到适合敦煌艺术发展的道路。而将敦煌的飞天元素提取到电子产品的配件及其衍生品当中,可以使消费者从当代的艺术中感受到传统艺术的永久独特魅力,形成独特的品牌效应,这是一种主体文化或依托主题文化因素发展的创意文化产业,既可以推动创意文化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将环保,创新等观念深入人心。
在手机配件的市场上,国内厂商还停留在制造阶段,生产上主要是简单的仿造外国配件设计。设计上外形单一,功能变化不大手机配件市场上急需中。本土设计的出现以突出重围。理论方面只限于从产业和技术的角度进行分析,但忽略了随着市场的日益细分,产业中的每一细节都是开发盈利的重要环节,尤其是敦煌壁画元素传统文化艺术的深入。研究及衍生产品开发。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艺术的创意和后续产品开发方面
手机配件设计缺乏流行性和时尚性,没有吸引力,后续的衍生产品开发意识薄弱。同时我们也要利用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产品相结合,使我们的手机配件变得丰富多彩,更具有中国特色。在后续开发方面我们会利用大量的敦煌壁画元素与手机外壳,吊坠,耳机,充电器等结合和利用。充分发挥敦煌壁画的特色。
(2)理论研究方面
篇12
战国简包括五里牌楚简37枚、仰天湖楚简43枚、杨家湾楚简72枚、长台关楚简229枚、望山楚简22枚、藤店楚简24枚、天星观楚简70枚、九店楚简344枚、随县楚简240多枚、临澧楚简数十枚、包山楚简448枚、秦家咀楚简41枚、石板村楚简4371片、郭店楚简804枚、新蔡楚简1300余枚等。
秦简包括云梦秦简1155枚(另有80枚残片)、天水秦简460枚、龙岗秦简283枚、木牍1方、杨家山秦简75枚、关沮秦汉简500枚、王家台秦简800余枚、周家台秦简389枚、木牍1枚、青川秦牍1枚等。
汉简包括敦煌汉简708枚(或云702枚、704枚)、居延汉简3500余枚、罗布淖尔汉简71枚、武威汉简600余枚、甘谷汉简23枚、银雀山汉简4974枚、武威医简78枚、木牍14方、马王堆汉简900余枚、木49枚、定县汉简一批、凤凰山汉简428枚、木牍9方、居延新简近两万枚、罗泊湾汉简十余枚、木牍5枚、阜阳汉简一批、大通汉简400枚、张家山汉简2787枚、胥浦汉简17枚、木牍2方、清水沟汉简一册(27枚)、散简14枚、悬泉置汉简35000余枚(有字者23000余枚)、帛书10件、纸文书10件、墙壁题记1件、尹湾汉简133枚、木椟24方、虎溪山汉简1000余枚、孔家坡汉简785枚等。
三国两晋简包括尼雅、楼兰简牍400余枚、纸文书728件、吐鲁番阿斯塔那晋木简1枚、南昌永外正街晋墓出土木刺5枚、木牍1枚、南昌阳明路三国吴墓出土木刺21枚、木牍2枚、鄂城出土三国吴木刺6枚、马鞍山出土三国木刺14枚、木3枚、武威旱滩坡出土东晋木牍5枚、高台晋墓出土木牍1枚、长沙走马楼出土三国吴简10万多枚等。
帛书包括斯坦因在敦煌汉代烽燧遗址中发现的几件帛书、长沙子弹库楚墓发现的“楚缯书”、敦煌马圈湾烽燧遗址出土的帛书1件、长沙马王堆3号墓出土的一大批帛书、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的帛书10件等。
简帛的整理与研究硕果累累
随着大宗简帛的相继出土和陆续公布,引起海内外学术界的极大兴趣和高度重视。据粗略统计,近百年来,经过海峡两岸和国外学者几代人的共同努力,已发表有关简帛研究的论著数千种。这些论著大体上可分为简帛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两个方面。所谓基础研究主要包括发掘报告、图版、释文、注释、语译、索引、字编、参考文献和论著目录等。而应用研究主要是应用新发现的简帛资料(包括简帛文字记载、实物以及器物、遗址、墓葬等),结合传世典籍研究当时的政治、法律、经济、军事、文化乃至科技、民族关系、中外关系、语言、文字、书法等各个方面。前者是前提,后者是归宿,两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正如张政先生为《简帛研究》题词所云:“辨析字形,理解文义,玑珠重联,审系篇题,终成图籍,补史之逸。”简帛的整理和研究,大体上是沿着这样的轨迹进行的。
1949年以前,主要集中于敦煌和居延汉简的整理和研究。首批敦煌汉简虽然首先由法国汉学家沙畹率先进行整理和考释,但作出最大贡献的应该首推我国学者罗振玉和王国维。二人于1914年合著的《流沙坠简》一书以及王国维后来发表的系列论文,不仅对每枚简文分类详加考释,而且应用新发现的简牍资料,撰写出许多研究汉代制度和西北史地的论文,尤其重视把敦煌汉简所记载的内容和汉代烽燧遗址的情况联系起来,力图尽可能恢复汉代烽燧组织系统的原貌。《流沙坠简》一书的精辟考释和王国维研究敦煌汉简的系列论文,不仅为当时的东西方学者所望尘莫及,而且至今仍不失为近代简帛学的奠基之作。和敦煌汉简迥然不同的是,首批居延汉简的整理和考释,一开始便是由中国学者负责的。起初参加的学者有马衡、向达、贺昌群、余逊和劳干等人,因为爆发,整理工作中辍。后由劳干一人完成全部整理和考释,先后于1943年和1944年在南溪石印出版了《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和《居延汉简考释·考证之部》。与此同时,劳干还发表了二十多篇研究居延汉简的论文。《释文之部》在变通《流沙坠简》一书的基础上,将居延汉简分为文书、簿录、簿籍、信札、经籍、杂类等六大类。《考证之部》和研究论文则沿用王国维所创立的“二重证据法”,进一步拓宽了研究领域,在居延汉简和汉代历史研究两个方面,均作出了巨大贡献。1949年以前,重要的论著还有《汉晋西陲木简汇编》、《罗布淖尔考古记》、《新获之敦煌汉简》、朝鲜古迹研究会《乐浪彩箧冢》、贺昌群《〈流沙坠简〉补正》、《烽燧考》、陈盘《汉晋遗简偶述》、《汉晋遗简偶述续稿》和劳干《敦煌汉简校文》等。
1949年以后,特别是随着七十年代居延新简和马圈湾等敦煌汉简的相继出土,居延和敦煌汉简的整理和研究仍呈方兴未艾之势,在应用简牍来研究历史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概括地说,在下列六个方面均有重大的突破:(一)、1956—1958年《内蒙古额济纳河流域考古报告》和1957年《居延汉简·图版之部》的出版,使人们第一次得知贝格曼田野发掘工作的详情,并能见到居延汉简的全部图版。(二)、1959年出版的《居延汉简甲编》(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首先公布了破城子、大湾、地湾、瓦因托尼、查科尔帖五地所出的1914枚汉简所属的出土地点。1980年出版的《居延汉简甲乙编》发表了首批居延汉简的全部出土地点,这对居延汉简的断简缀合、册书复原以及古文书学的研究,均有特殊重要的意义。(三)、早在《甲编》出版以后,就有学者曾撰文对《甲编》的释文进行补正,如陈直《〈居延汉简甲编〉释文校正》、陈邦怀《〈居延汉简甲编〉校语》、于豪亮《〈居延汉简甲编〉补释》等。当1980年《甲乙编》问世前后,又有许多学者接连不断发表有关补正释文的论著,如裘锡圭《汉简零拾》、于豪亮《居延汉简释丛》、谢桂华、李均明《〈居延汉简甲乙编〉补正举隅》等。从1979年起,为了整理新出土的居延汉简,谢桂华、李均明曾反复审读居延汉简各种版本的图版和释文,又得有机会见到尚未公开发表的居延新简的简影,于是将以往诸家释文逐一进行校订,最后编撰成《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一书,在释文的准确性上有显著的提高。(四)、众所周知,首批发现的一万余枚居延汉简,完整的册书仅保留下来两种,即由77枚简(其中2简无字)编联成的“永元器物簿”和由3枚简编联成的“永光二年候长郑赦予宁书”仅由此两种简册可知,居延汉简绝大多数原本都是用细麻绳编联的册书,出土以后,因为麻绳腐烂断绝,原来的册书都变成了一枚一枚的散简和断片。为此,森鹿三以为将已散乱的简牍恢复到册书的本来状态,至少恢复到接近原来的册书的状态,这是居延汉简研究的首要前提和基础工作。当1957年劳干《居延汉简·图版之部》出版以后,森鹿三将全部精力倾注到了“通泽第二亭食簿”(簿书)、卒家属廪名籍(名籍)等簿籍的复原上,率先开了复原居延汉简簿籍册书的先河。鲁惟一继承和发展了森鹿三的这种研究方法,出版了专著《汉代行政记录》,从居延汉简中复原出多种完整或基本完整的册书。对居延汉简的断简进行缀合和册书进行复原,其意义正如永田英正在《汉简的古文书学研究》一文中所总结的:(1)在居延汉简中,从全体上来看,簿籍简牍占绝大多数;(2)簿籍简牍和它们所记载的内容相应,各自具有固定的书写格式;(3)所有的簿籍简牍并不是孤立的个别记录,而是被编联成册书的;(4)以简牍的书写格式为标准,有可能将大量的简牍归类集成;(5)随着簿籍简牍的移送和传递,就有可能形成文书。这就开启了通往对简牍进行古文书学研究的道路。(五)1998年,台北出版了《居延汉简补编》。《补编》弥补了以往历次刊布的首批居延汉简的图版和释文均未能核对原简的根本缺陷。为了尽可能为字迹日渐褪色的原简保留最好的简影资料,而采用红外线设备等先进科学技术,使以往用肉眼和放大镜无法看出或看清的字迹,清晰呈现,从而对以往诸家的释文多有补正,在释文的准确性上又有新的突破和提高。(六)1994年中华书局出版《居延新简—甲渠候官》,全书分为上、下两册,上册为简牍释文,下册为简牍图版,除收录居延都尉所辖甲渠候官治所(7933枚)与甲渠候官所辖的第四部和第四燧(195枚)这两处遗址所获的全部简牍外,还收录了如下五宗简牍:(1)1982年在甲渠候官采集的散简20枚;(2)甲渠塞第四燧采集的散简67枚;(3)1976年在居延都尉三十井塞次东燧所获简173枚;(4)1972年居延地区采集的散简7枚;(5)1972年居延地区采集的地点不明的散简14枚,合计8409枚。《居延新简—甲渠候官》的出版标志着居延汉简从此进入新简和旧简结合,进行综合研究的新阶段。
与此相应,在1949年以后,中外学者研究居延汉简的论著不断出版问世,限于篇幅,在此不能一一列举。而林梅村、李均明《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大庭修《大英图书馆藏敦煌汉简》和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推出的《敦煌汉简》上、下册,则是研究敦煌汉简的重要论著。
另一方面,七十年代以后发现的简帛,诸如云梦秦简、马王堆汉墓帛书、尹湾汉墓简牍、郭店楚简等的研究也紧跟而上。(一)云梦秦简的释文公布伊始,便有许多学者撰写论文。据台湾东海大学吴福助教授统计,截至1995年止,已发表论著近千种。(二)马王堆汉墓帛书和竹木简,虽然还有三册没有发表,但经过20多年的整理和研究,业已取得丰硕的科研成果。其中,帛书《老子》、《黄帝书》既是整理发表最早的,也是海内外学术界特别关注和研究论著最丰富的两种帛书。《周易》和《易传》尽管发表时间较晚,但由于其在中国哲学思想发展史上的特殊地位决定,故一经发表,便成为研究热点。经过研究,《周易》经传和通行本大有不同。迄今为止,已发表的帛书研究成果数以百计。(三)尹湾汉墓简牍,仅就其数量而言,既无法与多达数万枚的居延和悬泉置汉简相比,也远不如云梦秦简、敦煌汉简、马王堆汉墓帛书和竹木简,但因为它们出自生前曾任东海郡功曹史的师饶墓中,不仅内涵异常丰富,而且特殊珍贵。自1993年春尹湾汉墓简牍发掘出土以后,连云港市博物馆为了将这批珍贵的简牍及早公诸于世,便迅速组织有关专家进行整理,于1997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了包括全部简牍图版、释文以及文物、发掘报告、简牍尺寸索引等在内的《尹湾汉墓简牍》一书。此外,还发表了廖伯源《简牍与制度——尹湾汉墓官文书考证》等专著、论文集、书法集以及论文近百种。(四)郭店楚墓竹简的发现,引起海内外学者的极大关注。1998年5月《郭店楚墓竹简》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后,立即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迅速形成国际性的研究热潮。专著、论文层出不穷,学术会议接连不断,研究成果丰硕可喜。(五)《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简牍》亦已面世。上海博物馆收购的楚简和期盼已久的张家山汉简也将出版。我们深信这些简牍定会成为学者们密切关注的新热点。
简帛研究的展望
百年来,简帛学不论在出土、整理还是研究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这是有目共睹的。与此同时,简帛研究中也存在诸多有待改进的地方,比如资料公布不及时、研究条件滞后、基础研究工作不扎实等。整理、研究简牍帛书资料,利用简牍帛书资料促进古代史研究,现在只是开始,可以说是方兴未艾,其深入发展还有待于将来。今后,这一领域发展的主要趋势是:
第一、加快简帛文献资料的整理和出版,缩短从简帛出土到全部公布之间的周期。目前,许多重要的简帛资料已出土很长时间,有的长达二十年,却由于种种原因,迟迟不见公布,严重影响了简帛研究的进程。希望各方人员通力协作,克服孤军奋战的局面,使出土简帛资料早日公诸于众。为了使大多数学者都能接触到简帛资料并应用于研究,每一批简帛资料除了出版包括图版、释文的精装本外,也应出版只有释文的简装本。另外,如同编纂《甲骨文合集》与《殷周金文集成》,简帛学界应考虑编纂包括秦汉简帛在内的《简帛集成》这样的大型资料汇编,为人们对分散的简帛资料进行比照和综合研究提供便利。
第二、借助现代高科技手段,改善研究条件。其一,采用红外线设备,提高简帛文字释读的准确率。其二,加快简帛资料数据库建设,使所有简帛资料都能上网进行图版检索和全文检索。这种方式比起手工翻检来,无论检索速度还是检索效果,都要优越得多。
第三、加强简帛资料研究的基础工作。主要包括发掘报告的撰写、简帛文字辨释、残碎帛片的拼接、断简缀合、简册复原、简帛内容考订、资料索引等。这方面的工作细微、琐碎,但它是研究的基础。有了翔实的发掘报告,有助于综合研究的开展。文字释读准确,内容理解无误,研究的结论才可靠。而残简碎帛的拼合与简册的复原,可以化腐朽为神奇,使无法利用的片言只语成为一句或一段有价值的资料。完备的资料索引,有助于研究者全面掌握每个课题的研究状况。
篇13
战国简包括五里牌楚简37枚、仰天湖楚简43枚、杨家湾楚简72枚、长台关楚简229枚、望山楚简22枚、藤店楚简24枚、天星观楚简70枚、九店楚简344枚、随县楚简240多枚、临澧楚简数十枚、包山楚简448枚、秦家咀楚简41枚、石板村楚简4371片、郭店楚简804枚、新蔡楚简1300余枚等。
秦简包括云梦秦简1155枚(另有80枚残片)、天水秦简460枚、龙岗秦简283枚、木牍1方、杨家山秦简75枚、关沮秦汉简500枚、王家台秦简800余枚、周家台秦简389枚、木牍1枚、青川秦牍1枚等。
汉简包括敦煌汉简708枚(或云702枚、704枚)、居延汉简3500余枚、罗布淖尔汉简71枚、武威汉简600余枚、甘谷汉简23枚、银雀山汉简4974枚、武威医简78枚、木牍14方、马王堆汉简900余枚、木49枚、定县汉简一批、凤凰山汉简428枚、木牍9方、居延新简近两万枚、罗泊湾汉简十余枚、木牍5枚、阜阳汉简一批、大通汉简400枚、张家山汉简2787枚、胥浦汉简17枚、木牍2方、清水沟汉简一册(27枚)、散简14枚、悬泉置汉简35000余枚(有字者23000余枚)、帛书10件、纸文书10件、墙壁题记1件、尹湾汉简133枚、木椟24方、虎溪山汉简1000余枚、孔家坡汉简785枚等。
三国两晋简包括尼雅、楼兰简牍400余枚、纸文书728件、吐鲁番阿斯塔那晋木简1枚、南昌永外正街晋墓出土木刺5枚、木牍1枚、南昌阳明路三国吴墓出土木刺21枚、木牍2枚、鄂城出土三国吴木刺6枚、马鞍山出土三国木刺14枚、木3枚、武威旱滩坡出土东晋木牍5枚、高台晋墓出土木牍1枚、长沙走马楼出土三国吴简10万多枚等。
帛书包括斯坦因在敦煌汉代烽燧遗址中发现的几件帛书、长沙子弹库楚墓发现的“楚缯书”、敦煌马圈湾烽燧遗址出土的帛书1件、长沙马王堆3号墓出土的一大批帛书、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的帛书10件等。
简帛的整理与研究硕果累累
随着大宗简帛的相继出土和陆续公布,引起海内外学术界的极大兴趣和高度重视。据粗略统计,近百年来,经过海峡两岸和国外学者几代人的共同努力,已发表有关简帛研究的论著数千种。这些论著大体上可分为简帛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两个方面。所谓基础研究主要包括发掘报告、图版、释文、注释、语译、索引、字编、参考文献和论著目录等。而应用研究主要是应用新发现的简帛资料(包括简帛文字记载、实物以及器物、遗址、墓葬等),结合传世典籍研究当时的政治、法律、经济、军事、文化乃至科技、民族关系、中外关系、语言、文字、书法等各个方面。前者是前提,后者是归宿,两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正如张政先生为《简帛研究》题词所云:“辨析字形,理解文义,玑珠重联,审系篇题,终成图籍,补史之逸。”简帛的整理和研究,大体上是沿着这样的轨迹进行的。
1949年以前,主要集中于敦煌和居延汉简的整理和研究。首批敦煌汉简虽然首先由法国汉学家沙畹率先进行整理和考释,但作出最大贡献的应该首推我国学者罗振玉和王国维。二人于1914年合著的《流沙坠简》一书以及王国维后来发表的系列论文,不仅对每枚简文分类详加考释,而且应用新发现的简牍资料,撰写出许多研究汉代制度和西北史地的论文,尤其重视把敦煌汉简所记载的内容和汉代烽燧遗址的情况联系起来,力图尽可能恢复汉代烽燧组织系统的原貌。《流沙坠简》一书的精辟考释和王国维研究敦煌汉简的系列论文,不仅为当时的东西方学者所望尘莫及,而且至今仍不失为近代简帛学的奠基之作。和敦煌汉简迥然不同的是,首批居延汉简的整理和考释,一开始便是由中国学者负责的。起初参加的学者有马衡、向达、贺昌群、余逊和劳干等人,因为爆发,整理工作中辍。后由劳干一人完成全部整理和考释,先后于1943年和1944年在南溪石印出版了《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和《居延汉简考释·考证之部》。与此同时,劳干还发表了二十多篇研究居延汉简的论文。《释文之部》在变通《流沙坠简》一书的基础上,将居延汉简分为文书、簿录、簿籍、信札、经籍、杂类等六大类。《考证之部》和研究论文则沿用王国维所创立的“二重证据法”,进一步拓宽了研究领域,在居延汉简和汉代历史研究两个方面,均作出了巨大贡献。1949年以前,重要的论著还有《汉晋西陲木简汇编》、《罗布淖尔考古记》、《新获之敦煌汉简》、朝鲜古迹研究会《乐浪彩箧冢》、贺昌群《〈流沙坠简〉补正》、《烽燧考》、陈盘《汉晋遗简偶述》、《汉晋遗简偶述续稿》和劳干《敦煌汉简校文》等。
1949年以后,特别是随着七十年代居延新简和马圈湾等敦煌汉简的相继出土,居延和敦煌汉简的整理和研究仍呈方兴未艾之势,在应用简牍来研究历史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概括地说,在下列六个方面均有重大的突破:(一)、1956—1958年《内蒙古额济纳河流域考古报告》和1957年《居延汉简·图版之部》的出版,使人们第一次得知贝格曼田野发掘工作的详情,并能见到居延汉简的全部图版。(二)、1959年出版的《居延汉简甲编》(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首先公布了破城子、大湾、地湾、瓦因托尼、查科尔帖五地所出的1914枚汉简所属的出土地点。1980年出版的《居延汉简甲乙编》发表了首批居延汉简的全部出土地点,这对居延汉简的断简缀合、册书复原以及古文书学的研究,均有特殊重要的意义。(三)、早在《甲编》出版以后,就有学者曾撰文对《甲编》的释文进行补正,如陈直《〈居延汉简甲编〉释文校正》、陈邦怀《〈居延汉简甲编〉校语》、于豪亮《〈居延汉简甲编〉补释》等。当1980年《甲乙编》问世前后,又有许多学者接连不断发表有关补正释文的论著,如裘锡圭《汉简零拾》、于豪亮《居延汉简释丛》、谢桂华、李均明《〈居延汉简甲乙编〉补正举隅》等。从1979年起,为了整理新出土的居延汉简,谢桂华、李均明曾反复审读居延汉简各种版本的图版和释文,又得有机会见到尚未公开发表的居延新简的简影,于是将以往诸家释文逐一进行校订,最后编撰成《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一书,在释文的准确性上有显著的提高。(四)、众所周知,首批发现的一万余枚居延汉简,完整的册书仅保留下来两种,即由77枚简(其中2简无字)编联成的“永元器物簿”和由3枚简编联成的“永光二年候长郑赦予宁书”仅由此两种简册可知,居延汉简绝大多数原本都是用细麻绳编联的册书,出土以后,因为麻绳腐烂断绝,原来的册书都变成了一枚一枚的散简和断片。为此,森鹿三以为将已散乱的简牍恢复到册书的本来状态,至少恢复到接近原来的册书的状态,这是居延汉简研究的首要前提和基础工作。当1957年劳干《居延汉简·图版之部》出版以后,森鹿三将全部精力倾注到了“通泽第二亭食簿”(簿书)、卒家属廪名籍(名籍)等簿籍的复原上,率先开了复原居延汉简簿籍册书的先河。鲁惟一继承和发展了森鹿三的这种研究方法,出版了专著《汉代行政记录》,从居延汉简中复原出多种完整或基本完整的册书。对居延汉简的断简进行缀合和册书进行复原,其意义正如永田英正在《汉简的古文书学研究》一文中所总结的:(1)在居延汉简中,从全体上来看,簿籍简牍占绝大多数;(2)簿籍简牍和它们所记载的内容相应,各自具有固定的书写格式;(3)所有的簿籍简牍并不是孤立的个别记录,而是被编联成册书的;(4)以简牍的书写格式为标准,有可能将大量的简牍归类集成;(5)随着簿籍简牍的移送和传递,就有可能形成文书。这就开启了通往对简牍进行古文书学研究的道路。(五)1998年,台北出版了《居延汉简补编》。《补编》弥补了以往历次刊布的首批居延汉简的图版和释文均未能核对原简的根本缺陷。为了尽可能为字迹日渐褪色的原简保留最好的简影资料,而采用红外线设备等先进科学技术,使以往用肉眼和放大镜无法看出或看清的字迹,清晰呈现,从而对以往诸家的释文多有补正,在释文的准确性上又有新的突破和提高。(六)1994年中华书局出版《居延新简—甲渠候官》,全书分为上、下两册,上册为简牍释文,下册为简牍图版,除收录居延都尉所辖甲渠候官治所(7933枚)与甲渠候官所辖的第四部和第四燧(195枚)这两处遗址所获的全部简牍外,还收录了如下五宗简牍:(1)1982年在甲渠候官采集的散简20枚;(2)甲渠塞第四燧采集的散简67枚;(3)1976年在居延都尉三十井塞次东燧所获简173枚;(4)1972年居延地区采集的散简7枚;(5)1972年居延地区采集的地点不明?纳⒓?4枚,合计8409枚。《居延新简—甲渠候官》的出版标志着居延汉简从此进入新简和旧简结合,进行综合研究的新阶段。
与此相应,在1949年以后,中外学者研究居延汉简的论著不断出版问世,限于篇幅,在此不能一一列举。而林梅村、李均明《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大庭修《大英图书馆藏敦煌汉简》和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推出的《敦煌汉简》上、下册,则是研究敦煌汉简的重要论著。
另一方面,七十年代以后发现的简帛,诸如云梦秦简、马王堆汉墓帛书、尹湾汉墓简牍、郭店楚简等的研究也紧跟而上。(一)云梦秦简的释文公布伊始,便有许多学者撰写论文。据台湾东海大学吴福助教授统计,截至1995年止,已发表论著近千种。(二)马王堆汉墓帛书和竹木简,虽然还有三册没有发表,但经过20多年的整理和研究,业已取得丰硕的科研成果。其中,帛书《老子》、《黄帝书》既是整理发表最早的,也是海内外学术界特别关注和研究论著最丰富的两种帛书。《周易》和《易传》尽管发表时间较晚,但由于其在中国哲学思想发展史上的特殊地位决定,故一经发表,便成为研究热点。经过研究,《周易》经传和通行本大有不同。迄今为止,已发表的帛书研究成果数以百计。(三)尹湾汉墓简牍,仅就其数量而言,既无法与多达数万枚的居延和悬泉置汉简相比,也远不如云梦秦简、敦煌汉简、马王堆汉墓帛书和竹木简,但因为它们出自生前曾任东海郡功曹史的师饶墓中,不仅内涵异常丰富,而且特殊珍贵。自1993年春尹湾汉墓简牍发掘出土以后,连云港市博物馆为了将这批珍贵的简牍及早公诸于世,便迅速组织有关专家进行整理,于1997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了包括全部简牍图版、释文以及文物、发掘报告、简牍尺寸索引等在内的《尹湾汉墓简牍》一书。此外,还发表了廖伯源《简牍与制度——尹湾汉墓官文书考证》等专著、论文集、书法集以及论文近百种。(四)郭店楚墓竹简的发现,引起海内外学者的极大关注。1998年5月《郭店楚墓竹简》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后,立即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迅速形成国际性的研究热潮。专著、论文层出不穷,学术会议接连不断,研究成果丰硕可喜。(五)《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简牍》亦已面世。上海博物馆收购的楚简和期盼已久的张家山汉简也将出版。我们深信这些简牍定会成为学者们密切关注的新热点。
简帛研究的展望
百年来,简帛学不论在出土、整理还是研究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这是有目共睹的。与此同时,简帛研究中也存在诸多有待改进的地方,比如资料公布不及时、研究条件滞后、基础研究工作不扎实等。整理、研究简牍帛书资料,利用简牍帛书资料促进古代史研究,现在只是开始,可以说是方兴未艾,其深入发展还有待于将来。今后,这一领域发展的主要趋势是:
第一、加快简帛文献资料的整理和出版,缩短从简帛出土到全部公布之间的周期。目前,许多重要的简帛资料已出土很长时间,有的长达二十年,却由于种种原因,迟迟不见公布,严重影响了简帛研究的进程。希望各方人员通力协作,克服孤军奋战的局面,使出土简帛资料早日公诸于众。为了使大多数学者都能接触到简帛资料并应用于研究,每一批简帛资料除了出版包括图版、释文的精装本外,也应出版只有释文的简装本。另外,如同编纂《甲骨文合集》与《殷周金文集成》,简帛学界应考虑编纂包括秦汉简帛在内的《简帛集成》这样的大型资料汇编,为人们对分散的简帛资料进行比照和综合研究提供便利。
第二、借助现代高科技手段,改善研究条件。其一,采用红外线设备,提高简帛文字释读的准确率。其二,加快简帛资料数据库建设,使所有简帛资料都能上网进行图版检索和全文检索。这种方式比起手工翻检来,无论检索速度还是检索效果,都要优越得多。
第三、加强简帛资料研究的基础工作。主要包括发掘报告的撰写、简帛文字辨释、残碎帛片的拼接、断简缀合、简册复原、简帛内容考订、资料索引等。这方面的工作细微、琐碎,但它是研究的基础。有了翔实的发掘报告,有助于综合研究的开展。文字释读准确,内容理解无误,研究的结论才可靠。而残简碎帛的拼合与简册的复原,可以化腐朽为神奇,使无法利用的片言只语成为一句或一段有价值的资料。完备的资料索引,有助于研究者全面掌握每个课题的研究状况。
 购物车(0)
购物车(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