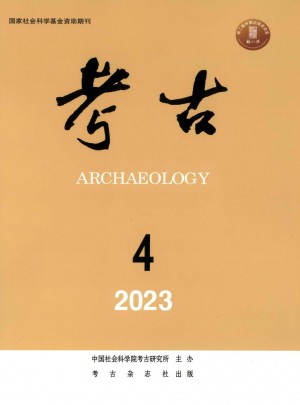引论:我们为您整理了13篇考古学发展史范文,供您借鉴以丰富您的创作。它们是您写作时的宝贵资源,期望它们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灵感,让您的文章更具深度。

篇1
云龙,西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设比苏县,唐为南诏所辖,宋(公元960年—公元1279年)称云龙赕,元至元二十六年(公元1289年)置云龙甸军民府,明洪武十七年改为云龙州。明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因盐设治,州府由旧州迁至雒马井(今宝丰),1913年改州为县,1929年迁县府至石门(今诺邓镇)。
自古水多桥亦多。云龙人民在历史的长河中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在众多的河流和山谷间修建了藤桥、溜索、独木桥、木梁风雨桥、铁链吊桥、石拱桥、浮桥等各式各样的桥梁。这些桥梁历史悠久、种类齐全、形式多样、结构独特,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科技价值和艺术价值,云龙故有“滇西桥乡”、“古桥家园”、“桥梁艺术博物馆”的美誉。
云龙拥有如此众多的桥梁,它们是如何产生和发展的呢?笔者通过田野调查和历史考证,从云龙盐业和矿业发展、明代的兵屯、等方面,探究了云龙古桥多样性发展的历史脉络及特点。
一、盐井开发与云龙桥梁的发展
盐业生产是一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产业。在中原,汉代盐和铁两大行业的生产问题曾引起当权者和利益相关者的争论,史称“盐铁论”。古代,海盐是难以运输到云南山区的,而盐是维系人类和动物生命不可缺少的物质,它在交通较为便利的中原地区都很紧俏,在交通极为不便的云南,就像金子一样的珍贵,先民们往往用很多的山货药材才能换取少量的食盐。因此,盐井的占有和开发权就像今天中东石油的占有和开发一样,是权力和富有的象征。
云龙历史就是一部盐的历史,同理也可以说,云龙桥梁发展史也是盐的历史。从下面的历史事实可以让我们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
公元8世纪中期,唐南诏势力崛起,逐渐形成地方政权。南诏比较重视发展盐业生产。唐人樊绰著《蛮书》载:“剑川有细诺邓井”。根据云南史志记述:公元794年,南诏政权置七节度,其中剑川节度领有沙追、讳溺、若耶、细诺邓、浪穹等地。又据《南诏野史·大蒙国》说,南诏初期有盐井40,后又有发展。《蛮书》卷七《云南管内物产》载:“安宁城中皆石盐井……城外又有四井……唯有览赕城内琅井盐洁白味美……泸南有美井盐……昆明城有大盐池……龙怯河水,中有盐井两所。剑寻东南有傍弥潜井、沙追井,西北有若耶井、讳溺井。剑川有细诺邓井。丽水城有罗苴井。长傍诸山皆有盐井……”[1]其中细诺邓井就是今云龙诺邓古村(2007年被评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盐业的发展推动了南诏、大理国政治、军事、交通运输的发展。
云龙是滇西著名的产盐区,盐业在云龙经济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明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十一月置云南盐课提举司。明史《食货志》:云南提举司凡四,曰黑盐井,曰白盐井,曰安宁井,曰五井。五井辖盐课司七,诺邓盐井盐课司,山井盐井盐课司,师井盐井盐课司,大井盐井盐课司,顺荡盐井盐课司,鹤庆军民府剑川州弥沙井盐课司,丽江军民府兰州盐井课司。
明初,明政府在诺邓设五井盐课司,“专理盐课”,下属顺荡、诺邓、师井、大井、山井五个盐课司。同时还在重要村邑及交通要塞设巡检司,如箭杆场(今团结、关平两乡)、十二关(今长新地区)、上五井(今石门镇及果郎、宝丰两乡各一部分)、顺荡井(今白石地区)、师井(今检槽地区、果郎乡一部分)等土巡检(可世袭的土官)负责管理。
1382年,明政府封曾投奔沐英大军攻取大理的段保为云龙土知州,经营澜沧江西面至怒江地区的广大地域。明初土知州、土巡检的设置基本结束了云龙境内一千多年的奴隶社会生产关系,代之而起的封建领主势力得以加强,而江东各地盐井及周边的封建地主经济也进一步发达。
篇2
二
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存在的几个现实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这一研究领域的发展。这些问题既有资料方面的原因,也有研究方法方面的原因。
资料方面,目前山东地区史前考古发掘资料中,多数侧重于陶器的统计分析,对石器基本上是粗线条的描述,尤其是在考古调查资料中,鲜有对石器的全面系统描述(指文字、线图、尺寸描述齐全者)。资料的不足在发掘器物的数量上体现的十分明显,例如山东龙山文化发表的资料中陶器数以万计,而石器仅有几千件,这种数量上的巨大差距说明了学者们以往对石器的重视程度不够。当然,这可能是时代的原因造成的,因为过去学者们偏重于对文化分期的研究以及文化谱系的建立,而在这方面陶器比石器更具优越性。另外,山东地区史前考古资料还缺少植物、动物鉴定的资料,虽然发表的考古发掘报告和简报中有些这方面的资料,但是这些资料多是零散的、少量的,不利于综合系统的研究。
研究方法方面,山东史前农业考古研究过去多从生产工具入手来研究农业的发展状况。这种方法上的单一化,不利于揭示农业生产发展的本质。在一些具体的研究上则存在以下几个主要问题:偏重整体叙述分析,缺乏个案深入研究;侧重农业发展史的研究,缺乏农业发展动因的合理解释;农业起源研究略显不足。
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研究存在上述问题,资料丰富程度不足是一个原因,而要深入研究这些问题,研究方法的改善才是关键。农业考古研究是一项综合的系统研究,多种方法的整体运用是必然趋势。史前农业考古研究没有文献资料可供参考,只能采用考古学资料进行分析。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新考古学的理论不断传入,为综合系统分析提供了有利条件。如今,考古学研究领域中正呈现"理论多元化、方法系统化、技术国际化"的趋势,农业考古研究亦是如此。国外一些先进的技术方法,大大地提高了资料获取程度,同时也相应地扩展了研究的领域。农业考古学应该以此为契机,丰富自己的研究理论,改进技术方法。这其中民族学、经济学、数学统计分析的方法尤为重要、民族学中有关原始民族以及现代晚进民族的资料是进行史前农业考古学研究的"活化石",这些资料可以为史前农业研究提供参考;经济学中有关社会经济发展研究的原理,对史前农业发展进程的分析具有借鉴意义;数学中统计方法对史前农业进行量化研究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正如上文所讲,过去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学研究注重整体叙述分析,缺乏个案深入研究,而个案深入研究中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式就是量化研究。整体叙述分析可以从整体上把握史前农业的发展进程,但要想深入了解各个时期的农业状况则必须采取量化分析的方式,因为量化分析能够更清楚地了解各种因素的比例关系,发现隐藏于实物资料背后的深层次动因。例如,我们过去将目光过多地集中于生产工具的发展变化上,从生产工具的变化角度寻找社会变化发展的原因,但是近年来的研究成果表明春秋以前金属生产工具在农业生产中并未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农具不是农业生产的唯一"指示器"(11)。如果从量化的角度来分析,就可以更清楚的看到这一点。农业考古研究不仅要复原古代农业发展史,还要对此进行解释。既然农具不是农业生产的唯一"指示器",那么就应该找到另外的"指示器"。从山东地区史前遗址的发现情况能够大致看出这方面的因素。山东地区史前文化谱系比较清楚,从早到晚依次为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目前已发现的遗址数量中,后李文化为10余处,北辛文化100余处,大汶口文化500余处,龙山文化1300余处,岳石文化近300处。后李文化和北辛文化中打制石器还占一定比例,而到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时期磨制石器已占绝大多数。在农业生产工具没有质的变化的情况下,社会如何支持大量增加的人口就值得深入分析了。山东龙山文化时期遗址达1300余处,表明此时人口已大量增加,要解释这一现象还需联系当时的社会发展情况。龙山文化时期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城址大量增加、文字出现、等级分化加剧,这一切又不同于西方的文明模式,只能从中国的历史实际进行分析。从综合大型工程,如城址、祭坛的建筑可以获知社会组织管理职能的加强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管理职能也会反映在农业生产的分工协作上,从而提高了生产效率,扩大了农业生产。另外,农作物栽培技术的改善也会相应的增加产量,促进农业发展。因此可以说农业的发展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非单一变量的原因。可见,只有在量化研究的基础上,才能全面而深刻地揭示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因。
总之,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研究无论是从整体叙述上还是从个案分析上,都要求我们必须采取多种方法并转换传统的研究视角,从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出发,在多种因素综合量化分析的基础上,揭示中国农业发展的规律,阐释中国文明的本质动因。 三
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研究虽然存在资料不足的现实情况,但是这并不妨碍农业考古学研究的深化,而且这种情况在不久的将来会逐步得到改善。现在重要的是能够使广大考古工作者特别是发掘者在意识上形成主动收集农业考古学资料的观念,带着科研目标去从事考古发掘工作。考古发掘是收集资料的主要方式,而且也是获得科学资料的关键。近年来,有关考古学分支学科的确立使得考古资料的信息量大增,这与发掘者的主观意识是分不开的。在农业考古学研究中植物考古学、动物考古学等分支学科的确立,让更多的考古工作者意识到了资料收集工作的重要性,因为研究的深入对考古资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这在传统考古学资料中有些是无法获得的。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学中植物硅酸体分析方法的应用以及相关研究的开展(12),为加强农业考古学资料的收集工作创造了条件。无疑新方法的应用扩大了研究的范围,也提高了农业考古学资料收集的精细化程度。
在资料不断丰富的条件下,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学研究有望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突破。首先是农业生产工具的研究,在定量分析的基础上,能够了解个别区域乃至整个山东地区生产工具的特点和具体的生产方式,不同地区、不同地域的生产工具是不同的,这与土质以及环境有直接的关系,而只有深化个案研究,才能了解地区间的差异。其次是农业起源的研究,多种理论与方法的综合分析,是其取得突破的保证。农业是如何起源的问题历来为学术界所关注,山东地区地理环境较为封闭,其区域的系统研究必将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这里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等的理论与方法在分析过程中的综合应用,有助于问题的解决。最后是农业与文明的关系研究,在其他研究不断深化的前题下,能够取得长足的进展。农业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保证,但农业的发展不一定就能导致文明的产生。这里任何单一的因素都无法解释文明的产生。因此,综合分析山东地区史前农业发展过程并结合相关领域的研究可以为文明的产生与发展提供合理的解释。
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研究的问题还相当多,这些问题的解决还有赖于农业考古学理论、方法、技术的改进。国外的一些研究理论、方法、技术是在总结西方实践的基础上提出的,对于中国的考古学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是还需中国实践的检验。因此,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学研究在应用这些方法进行研究的时候,对总结中国自己的农业考古学研究理论与方法具有重要意义。
注释:
(1)陈文华:《简论农业考古》,《农业考古》1984年第2期。
(2)吴诗池:《山东新石器时代农业考古概述》,《农业考古》1985年第1期。
(3)吴诗池:《海岱文化区的史前农业》,《农业考古》1985年第1期。
(4)吴诗池:《综述山东出土的农业生产工具》,《农业考古》1990年第1期。
(5)石敬东:《从出土文物看枣庄地区的史前农业》,《农业考古》2000年第3期。
(6)房道国:《济南地区古代农业考古概述》,《农业考古》1996年第1期。
(7)陈淑卿:《海岱地区龙山文化生产工具的类型学考察》,《辽海文物刊》1997年第2期。
(8)任相宏:《岳石文化的农具》,《考古》1995年第10期。
(9)这类文章很多,主要有:
何德亮:《论山东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养猪业》,《农业考古》1986年第1期。
刘俊勇:《试论东夷史前经济》,《中原文物》1994年第4期。
何德亮:《山东史前时期自然环境的考古学观察》,《华夏考古》1996年第3期。
(10)佟佩华:《海岱地区原始农业初探》,《庆祝山东大学考古系成立三十周年论文集》(待刊)。
何德亮:《试论山东地区的原始农业》,《庆祝山东大学考古系成立三十周年论文集》(待刊)。
(11)白云翔:《我国青铜时代农业生产工具的考古发现及其考察》,《农业考古》2002年第3期。
(12)有关山东地区史前植物硅酸体及其相关研究的论文主要有:
王克林、吴加安:《尉迟寺遗址硅酸体分析-兼论尉迟寺遗址史前农业经济特点》,《考古》1998年第4期。
靳桂云:《山东临淄田旺龙山文化遗址植物硅酸体分析》,《考古》1999年第2期。
篇3
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古代艺术品。古代艺术品的来源不外乎两大类,一类是历代流传下来的传世品;另一类是经过科学的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得到的艺术品。传世艺术品往往是中国古代艺术发展史研究的主要材料。然而,传世艺术品有两个致命的缺陷,一个是其确切的时代难以认证,给研究工作增加了难度;另一个更突出的问题是,对古代艺术品出于各种不同目的的仿制甚至作伪。许多前代的青铜器、玉器、书画等艺术品都或多或少地被后人所仿制。因此,传世艺术品不能成为艺术考古学的主要研究对象。
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植根于考古学,是运用科学的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的手段得来的。它只是数量、品种众多的考古学研究对象的一小部分。以此为前提,我们可以通过对已有定论的考古学研究对象的分析,逐渐剥离出非艺术性的物质产品,较为合理地勾画出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面貌。作为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其首要条件必须是人类运用自己的双手劳动创造的产物,这样就从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中排除了与古代人类活动有关的“未经人类加工的自然物”,如“各种农作物、家畜、及渔猎或采集所获得的动植物的遗存等”;同样,从艺术品所具有的审美和情感性出发,考古学研究对象中的灰坑、窖藏、矿井、水渠、壕沟等遗迹,虽然都是人工创造物,但仅具实用功能,或服务于生产生活,或用于战争的防御,很难激起人的审美感受,因此,也不能成为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至于古代人类以艺术手法加工制作的陶瓷器、玉器、青铜器、漆器、金银器和各类装饰品等工艺美术品,以及岩画、壁画、画像石、画像砖、雕塑等艺术作品,无疑是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然而,考古发掘出土的各种生产工具、日用器具,以及石刻、封泥、墓志、买地券,甲骨、简牍、纺织品、钱币、度量衡器等,都具有了作为艺术品的首要条件,即人工创造性的特征,但这些物品却决非都是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
一、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分类
由于艺术考古学是考古学的一个特殊分支,是一门在艺术学和考古学蓬勃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交叉科学,其研究对象既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艺术学科研究古代艺术产生、发展、演变规律的重要资料,因此,对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分类,要以考古学的分类方法为主线,同时参照艺术分类法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资料,其中,最主要的是古代人类劳动创造的物质性遗存,一般分成遗物和遗迹两大类。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则是考古学研究对象中人类精神文化创造的遗存,同样也可以分为艺术遗迹和艺术遗物两大类。
艺术遗迹是指经过古代劳动人民艺术性创造的历史遗留,是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重要组成部分。艺术遗迹主要是古代的建筑遗存,在中国可以分成地上建筑和地下建筑两大类。中国古代的地上建筑大多利用各种木料,以斗拱、榫卯结构建造。由于自然的和人为的种种因素的毁坏,保存在地面上的早期(唐代以前)木结构建筑物几乎绝迹,仅存部分建筑物的残缺构件,唐代以后的古建筑遗迹也只有寺观、塔、石阙、石窟寺、桥梁等几类。中国古代的地下建筑是皇室贵族建造的坟墓,以砖、石为材料,大多模拟当时地上建筑的风貌,但趋于简率。相比较而言,考古调查和发掘出土的有关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实物资料并不丰富,但作为建筑附属装饰的壁画和雕塑却独树一帜,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艺术遗迹的分类便以壁画和雕塑为主。
艺术遗物主要是指那些经过艺术加工创造的绘画、雕塑、碑刻书法作品以及实用和审美相结合的工艺美术品,其中工艺美术品无论在数量、种类,还是在艺术题材和艺术成就上都远远超过前者。艺术遗物中的绘画艺术品,主要有帛画与绢画、木版画与木简画、卷轴画等几类。艺术遗物中的雕塑艺术品,主要有墓葬和遗址出土的陶塑、瓷塑、木雕等几类。书法是文字的书写艺术,从最初刻划在陶器上的符号到商周的甲骨文、金文,战国秦汉的货币文字、印章文字、石刻文字、封泥文字、瓦当文字、铜镜文字、简帛文字等,都是成熟的书法艺术出现的基础和源泉。中国古代的工艺美术品,按质地和装饰手法可以细分为陶器艺术品、玉器艺术品、铜器艺术品、漆器艺术品、瓷器艺术品、丝织艺术品、金银艺术品和骨雕、牙雕艺术品等。中国古代艺术品的种类纷繁复杂,除了上述绘画、雕塑、碑刻书法和工艺美术品之外,还包括音乐、舞蹈、乐舞百戏、瓦当、剪纸、面塑等其它艺术品。
二、艺术考古学的研究方法
艺术考古学是一门建立在考古学和艺术学基础上的新兴的交叉或边缘学科,因此,凡是考古学和艺术学的研究方法都能在艺术考古学的研究中得到运用和借鉴。目前,对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尚未衍生出一套科学的方法论体系,但卓有成效的研究方法却随着考古发掘出土的古代艺术品的日益增多而逐渐露出端倪。一般来说,艺术考古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来源于对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文化人类学、图像学等研究成果或研究方法的借鉴,以及对中国古代历史文献资料的运用。
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是研究资料重要的分类排比方法。正像历史学家从一页页古代文献记录中寻找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轨迹一样,考古学家也正是从这一层层的古代人类遗留下来的文化堆积层中,艰难地复原古代社会的面貌,使它们成为科学的研究资料。考古地层学给古代艺术品贴上了时代的标签,恢复了历史的真实。考古类型学是考古学研究中整理分析资料的一个重要方法。考古类型学在艺术考古学上的应用,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通过对古代艺术品形态和装饰题材的分析研究解决年代学的问题,从而使考古资料有更严密的科学性。另一方面,通过对大量材料的分析、排比后,归纳出古代艺术品的内容题材和装饰手法的种类,整理出一套完整的、系统的研究资料。
文化人类学是解决原始艺术问题的一把钥匙。如何尽可能准确地解释史前艺术品,就需要运用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和方法。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成果是多方面的,既有对史前原始艺术、有史时期野蛮民族和现存少数民族艺术创造的研究成果,又有与古代艺术创造有密切关系的人类生活状况、伦理道德观念、等物质文化和人类意识形态方面研究的成就。
篇4
学科定义涉及学科的研究对象,同时,一个学科性质的准确认识,也需要涉及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通过学科之间的关系梳理,可以突出学科的特征,同时也可以完善学科自身的理论建设。在关于美术考古学科关系的认识中,目前学者较多涉及的是与考古学、美术学、社会学、历史学、图像学等学科的关系,这其中涉及学科的本源、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学科的意义等诸多方面,涉及面不可谓不广、不可谓不具体。遗憾的是,在这些关系的讨论中,基本上没有考虑到美术考古与宗教美术之间的特殊关系。美术考古与宗教美术,不仅在研究对象上有相同之处,而且在研究资料的获取上也有相同之处;同时,在接受宗教信仰的影响上也有相同之处。因此,我们提出美术考古的叙事特征和与宗教美术的学科关系作为理论深入的探讨视角。
一、与研究对象相关的叙事逻辑
这是一个关于叙事逻辑的学科定位问题。我们认为,美术考古如果作为分支学科看待,那么,从叙事逻辑角度看,它不是考古学的分支学科而应当是美术学的二级学科。
首先,美术考古是将研究对象作为美术史现象来描述的。“以田野考古发掘和调查所获得的美术遗迹和遗物”[1](p5)是美术考古的研究对象,在美术考古的研究过程中,这些美术遗迹和遗物转化为美术发展史上的叙事遗存,围绕美术遗迹和遗物展开的研究是关于构图、造型、色彩和主题、风格、艺术进步等美术学科范畴的研究。以我国西域龟兹石窟为例,在考古学的研究中,它是关于石窟的考古对象;而在美术考古的研究中,它就是石窟艺术的研究对象,研究者是将它作为美术现象来研究的,学者们从龟兹石窟感受到了多元化的艺术影响。比如,希腊艺术的影响:“在龟兹石窟的早期壁画中,人物显得非常突出,与后期山水鸟兽等附加景物的比例较大有明显的不同,这就是受希腊以人为本艺术思想的表现。有些形象与希腊神话传说似乎也有联系,如克孜尔石窟新1窟中的人面兽身的金翅鸟,荷马史诗中也有生动的描写。被学术界所注目的龟兹壁画,显然也是有希腊艺术影响的痕迹。希腊艺术是推崇的,认为这是健康、力量和美的象征。龟兹艺术家接受了这样的审美观点,而且也对小乘佛教的禁欲主义给予了突破。”[2](p137)这些研究内容,已经完全是在美术学的学科范围中进行。其他著名的敦煌石窟艺术、汉画像石墓葬艺术等,在进入美术考古视野后,都是作为美术发展史上的美术现象、叙事风格和艺术成就来研究的。
其次,考古学的学科方法并不支持美术考古的研究趋势。目前学术界中,不论是将美术考古归之于考古学学科还是将美术考古归之于美术学学科,学者们都希望美术考古拥有更多的研究方法和更加广泛的研究领域,但是,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并不支持美术考古这种具有扩张性的发展要求。中国传统的田野考古学的主要研究方法是地层学和考古类型学(标型学、器物形态学),这两种方法都借鉴于自然科学的手段和理念。自然科学是以物为研究标的的特性,这一基本点决定了田野考古学只能是“见物不见人”。美术考古如被作为田野考古学的一个分支,虽然研究对象是考古学研究中的特殊对象——美术作品,但是它从属于田野考古学的关系决定了其在方法论上必然是以地层学和考古类型学为主要研究手段,在研究过程中强调过程的客观性,禁止运用描述性语言,从而忽视了这种特殊人工制品所具有的主观性内容。有学者认为:“许多考古人不做研究,将考古发掘报告当作研究成果,那是不妥的。任何学科都离不开研究,否则就不是什么学问了。而且,考古界禁止用描述性语言也是错误的。”[3]在强调客观性的制约下,美术考古归于考古学缺少可操作性。
我们还可以从一些考古学前辈和权威性的观点中得到旁证。比如,前辈夏鼐认为:“作为考古学的一个分支,美术考古学是从历史科学的立场出发,把各种美术品作为实物标本,研究的目标在于复原古代的社会文化。这与美术史学者从作为意识形态的审美观念出发以研究各种美术品相比,则有原则性的差别;由于美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在年代上上起旧石器时代,下迄各历史时代,所以它既属于史前考古学的范围,也属于历史考古学的范围。又由于作为遗迹和遗物的各种美术品多是从田野调查发掘工作中发现的,所以美术考古学与田野考古学的关系也相当密切!”[4](p9)目前,“复原古代的社会文化”已经不能覆盖美术考古的全部研究成果,相反,“作为意识形态的审美观念”则成为一个重要的内容,我国目前美术考古取得的学科影响主要是在美术学领域。其一,美术考古的研究成果极大地丰富了美术史的研究内容。在美术考古发挥影响之前,我国美术史的研究依赖于传世的美术作品和相关文献,这些作品和文献在传播过程中指导创作,形成流派,后人由此而产生的理解也直接推动美术理论的发展。但是,在美术考古学科形成后,情况发生变化,大量的美术考古作品进入美术史的研究领域,不仅增加了传统美术的作品数量,而且美术史的理论认识也得到了普遍提高。在目前流行的美术史教科书中,美术考古的内容已经进入到了所有朝代美术发展的认识中。其二,美术考古的研究成果提出了新的美术史研究模式。对于传世美术作品的研究,美术史更多的是依靠传统的文化研究模式,比如知人论世的考释,比如师承关系的梳理,等等。对于美术考古作品,考古学的地层学方法和类型学方法则被学者们热情地引入,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等学科的理论也被学者们广泛地运用,目前甚为流行的图像学、叙事学等,皆为美术考古研究常用方法。其三,美术考古的研究成果极大地提高了美术史研究的学术影响。这一点最好理解,美术考古将美术史的研究进入到石窟艺术、墓葬艺术、岩画艺术等考古遗存的领域,美术史上的许多空白被填补,许多文化遗存得到了更深入的理解,美术史在作出贡献的同时也提高了自己的学术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
因此,我们认为美术考古不应作为考古学的分支学科,而应当作为美术学的分支学科。通过对美术考古定义的讨论,我们提出一个求教大方的表述:美术考古是一门以田野考古发掘和调查所获得的美术遗迹和遗物为研究对象、在美术史层面上展开研究活动的美术学分支学科。
二、与宗教美术相关的叙事特征
这是一个从叙事特征角度讨论学科关系的问题。
首先,从逻辑关系上对叙事特征的讨论。
从形式逻辑的角度看,美术考古与宗教美术在概念上存在的关系是交叉关系。这样的关系与全同关系不同,具有反自返性、对称性和非传递性的性质。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学术界并没有注意到它们之间存在的紧密联系。实际上,在它们的研究对象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与宗教信仰有关,同时,它们的研究对象基本上是通过考古手段获得的,因此在研究方法上也具有许多相同的地方。
从叙事特征看,美术考古的研究对象主要有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因为宗教信仰原因而成为考古对象的,如墓葬艺术作品、石窟艺术作品等;第二部分是因为社会动乱、自然灾害等原因而成为考古对象的,如古建筑遗址、被掩埋的艺术作品等。这两部分作品中,从目前的研究条件看,宗教信仰原因的考古对象占有着极大的比重。这一现象,也与我国传统文化的延承有关。自三代开始,人们就将与自然、先人有关的祭祀活动和与自己有关的埋葬活动作为了一项重要的社会活动,以后的各类宗教思想发展不仅没有降低这项活动的重要性,而且还从生命的价值、生命的不灭和生命的转化等方面予以丰富和细化。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宗教信仰深入于艺术活动之中,留下了丰富的美术作品。
宗教美术的研究对象也有两部分:第一部分是通过考古手段而获得的美术作品,第二部分则是通过代代相传的方式而保存、流传的传世作品。与美术考古一样,宗教美术的第一部分占有极大的比重,而且第一部分的作品与美术考古的第一部分作品完全重叠,如墓葬艺术作品、石窟艺术作品等。这些美术作品都是通过考古的手段而获得,这就使得这两门学科有了更加紧密的学科关系,我们因此而可以提出这样的关系命题:对于这部分作品,美术考古和宗教美术是关于宗教信仰创作的美术活动。“美术考古”和“宗教美术”是主项,“关于宗教信仰创作的美术活动”是谓项,主项之间的关系是对称性的性质。美术考古和宗教美术所具有的对称性关系,虽然是有条件的,不能覆盖两学科的所有内容,但是考虑到这部分重叠的内容具有很大的比重,而且这部分作品中优秀作品的比重也很大,所以这样的对称性关系使得两学科的共同性有了特别的意义。在建立美术考古与宗教美术的关系命题之后,我们就可以从许多共同性的方面来深入思考它们的学科性质了。
其次,关于美术作品埋葬方式的叙事认识。
在通过考古手段而获得的美术作品中,其埋葬方式毫无疑问是美术作品完成叙事的重要内容,可是这一点目前没有深入的研究。在目前美术考古与宗教美术的研究论文中,研究对象的确定常常是侧重于从作品的发现角度来认识的,即考古学的角度。我们则认为,作品的埋葬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角度,这是一个关于作品本体的角度。当然,作品埋葬和作品发现都是属于作品存在的范畴,作品发现也已经反映了作品的部分埋葬情况,但是埋葬的角度是一种直接性的观察,可以更有针对性地收集和反映相关信息。另一方面,就作品的流传而言,作品的埋葬是一个主动的行为,原作品所有人的主观愿望可以得到最大可能的实现;而作品的发现,则可能是一个被动的行为,其中的一些环节是原作品所有人不可预期、不可掌握的,在大多数情况下甚至是与原作品所有人的愿望是没有关系的,极端情况下还可能是完全相反的。如果作品的发现不考虑这些因素,那么认识原作品所有人的创作就有了一个信息损失、甚至歪曲的可能。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比如汉墓壁画,墓主人将反映自己社会地位、日常生活和对另一个世界想象的绘画作品置于自己的墓室之中,他的目的是表现自己的长生思想。对他而言,长生思想的表现是一个长生行为,是对长生信仰的体验,同时,这一定是一个个人的行动。他绝对没有考虑到这样的现象:考古学的发掘活动,发现了他的行为或研究了他的思想。也就是说,墓主人墓葬绘画行为的目的只是后人理解中的一部分内容,另外的内容为后人所加。墓主人的内容和后人的内容之间的叙事结构完成,在新信息得到的同时,也可能会因为叙事结构的转化而损失了一定的信息,比如误解,比如疏忽。所以,作品的埋葬与作品的发现,是一个存在一定意义差别的不同角度。
作品的埋葬涉及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作品为什么存在?关于宗教信仰创作的美术作品,其创作是在信仰的指导下完成的。作品的所有人相信另一个世界的存在,个人的魂魄并不随着自己的生命结束而结束,而是在另一个世界能够继续,所以他要为那个世界的存在而作这个世界的准备,因此他的行为就涉及美术考古和宗教美术的研究对象——具有宗教色彩的美术作品。这样的美术作品又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专门创作而直接参加宗教行为的作品,如石窟中的造像和壁画;一种是之前创作而间接参加宗教行为的作品,如墓葬艺术中的一些帛画、雕塑、冥器等作品。这两类作品就创作过程而言,有着不同的创作性质,第一种是宗教行为性质的创作,完全是在宗教信仰的指导下进行,为宗教体验服务是它的唯一目的;第二种是世俗行为性质的创作,在创作过程中并不一定接受宗教信仰的指导。这两类作品能够有叙事上的同构,是因为埋葬活动提供了条件,为宗教信仰服务是作品完成整个叙事过程之后才得到的创作意义。这两类作品在考古学的活动中,都是以历史遗存的形式出现,就作品的发现而言,它们是以相同形式的遗存出现的,它们的主题也都是为墓主人或供养人的宗教信仰服务的创作行为。但是,宗教行为的创作行为和世俗行为的创作行为是存在着区别的,世俗行为成为宗教行为必须有一个结构演变的过程。
从逻辑关系角度看,美术考古与宗教美术有着部分对称性的关系,其意义是肯定两学科的共同性,从共同性的角度出发认识它们的优秀作品;而从埋葬角度出发,美术考古与宗教美术被考虑的则是两学科之间存在的差异性。当然,这个差异性是部分的,而且是在共同性的前提下展开的,目的是从两学科的关系层面上思考学科性质。但是,如果我们在了解、分析埋葬美术作品时没有考虑到美术考古与宗教美术学科之间的差异,那我们的认识必然是不全面的,甚至是有错误的。
再次,关于叙事意义的理论认识。
叙事作品是一个动态的意义生成系统。[5]通过学科逻辑关系的认识,我们可以从逻辑角度认识美术考古与宗教美术之间所存在的共同性;通过作品埋葬角度的认识,我们可以从作品存在的角度认识两学科之间存在的差异性。同时,两学科的结合思考还可以在操作层面上提供可以深入的理论意义。这个意义,就是在认识美术考古和宗教美术学科特征的基础上突出两者结合思考后的指导意义,即强调宗教美术作品和与之相关的美术考古作品所具有的叙事意义。
其一,叙事主题的单一性(或集中性)。
在宗教美术作品和与之相关的美术考古作品中,叙事的结构往往都显得非常宏大,几乎所有的构图都试图包括天上和地下、凡间和世外,这是宗教信仰指导的必然结果。如我国最早的黄帝图像就出现在山东武梁祠的画像石中,与他同时出现的还有孔子等先秦圣人,他们之上就是西王母的图像,墓主人用这样的构图说明西王母对世界的控制和自己对西王母无所不及的期待。无所不及是一个多么大的结构,墓主人能够在有限的画面上和有限的手段等条件下完成这样大的结构吗?显然这是一个充满着矛盾的要求,但是宗教美术可以很轻松和很合理地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是叙事主题的单一,或叙事主题的集中。在所有的宗教美术作品中,作品的主体都是至上神或主宰这个世界的神灵。在构图上,这个主体占据着作品的最重要位置和最大的比例,甚至是唯一的形象,比如我国四川和北方河南、山西的一些大型石窟中,常常主体就是一尊佛的造像。以单一的形象反映丰富的世界,在世俗美术创作中是非常难办的,似乎有悖于一般的艺术创作规律,但是这在宗教美术创作中却是普遍的现象。在宗教美术创作中,至上神与其所代表的世界表现的是终极关怀,艺术审美感来自信仰经验。如此,净化的世界也同时产生了简化的世界,叙事主题自然就显得单一,显得集中。当美术考古的作品涉及宗教美术的范畴时,相关的叙事同样是沿着这样的路径进行的,丰富的世界可以作为创作的背景存在,但就作品本身而言,其主题是单一的,是集中的。宗教美术作品的叙事主题单一、集中的特点,可以充分反映、同时也充分论证了宗教行为的性质和影响的存在。
其二,情节的真实性。
宗教美术是描写另一个世界的,与现实世界对照,它是不真实的。但是,宗教美术作品能够存在的理由却是来自于宗教经验,即这些作品的内容是真实的。这样的真实在作品中得到了普遍支持,即作品表现了情节的真实性。情节的真实性当然是来自于对现实生活的反映,宗教经验对这样的真实是支持的态度。宗教美术作品的构图体现着这样的“真实性”。在我国神话传说中,女娲是一个大神,有着极高的地位。我国早期的历史书籍中,几乎都有关于女娲的文字记载,在各地的民间传说中,女娲也有着极为丰富的资料。关于女娲神话的发展,学者们的研究是将女娲的神格分为始祖母神格和文化英雄神格两大类。为什么女娲在这两方面作出贡献?因为她是女神,这一点充分表现在艺术形象中。她能够如现实世界中的女性一样造人,而且她有着许多神奇的造人方法。主要有三种造人法,即化生人类、抟土作人和孕育人类[6](p29)。就神话的流传而言,女娲的这些情节都是真实的。汉画像石中,女娲所拥有的与生育有关的情节也是真实的。在汉画像石里,女娲的形象一般被描写为人首蛇身状,有着非常浓郁的原始气息。因为在原始社会,女性的最重要任务就是生育,蛇是卵生动物,生育力特别强,女娲蛇身就有了这方面的思想寄托。在原始神话中,蛇的生育本领往往要被移植于造物的神话里,许多造物的大神因为本领大、功劳大而与蛇产生联系。在造物的神话人物中,烛龙是个大神,他就有着蛇的形态。
因此,在宗教美术和美术考古的作品中,情节的真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叙事特征,这一点与世俗美术有相似的地方,但它们的区别也是明显的,即宗教美术并不是依靠写实来达到真实的,也不一定是依靠夸张来达到真实的,更多的依靠联想,依靠联想来获得情节的真实,联系最直接的说明,就是物象的符号化。
其三,物象的符号化。
在宗教美术作品中,物象符号化的手法无处不在,每一个物象都拒绝随意的理解,必须从某一个已经存在的特定的概念来入手,从而得到物象的象征意义。一是因为宗教美术有着强大的象征体系,天边的云气是象征仙界的符号,飞翔的鸟是象征使者的符号,地面行走的神兽是象征宗教行为某个过程的符号,每一个物象都与象征体系有着对应的关系,有了符号化的运用,物象的意义不仅更加明确,而且接受也有了流畅的表达过程;另一个原因是宗教美术所包含的宗教仪式内容,仪式支持宗教美术,但对艺术创作有约束的要求,这个要求并不是生硬的,而是通过符号的联系来实现,这样的联系在宗教的象征体系中就产生了艺术的联想。当然,我们也同时注意到,世俗与宗教有着并不完全相同的象征体系,所以宗教物象与世俗物象是有区别的。比如蟾蜍,在宗教的象征体系中,它是长生的物象,使信徒联想到与长生有关的美好事物,于是蟾蜍就可以与嫦娥有了联系。特别是在汉代,画像石中有将嫦娥与蟾蜍联系在一起构图的现象,而且这种图像非常普遍。但是在世俗世界,因为形象的问题,嫦娥和蟾蜍是被分开的。如白居易的《虾蟆》诗,不仅对嫦娥与蟾蜍作了区别,而且还特别提出害怕将虾蟆拿来联系嫦娥,认为这样会玷污嫦娥的美名:“常恐飞上天,跳远随妲娥。往往蚀明月,谴君无奈何!”因此,物象的符号化不仅反映出宗教美术的叙事路径,而且也可以很好地说明宗教美术区别于世俗美术的艺术特征。
三、结语
综上所述,就学科性质的认识而言,美术考古与宗教美术之间存在的关系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命题,这两门学科的共性可以使我们在认识学科性质上寻找到诸如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方面的逻辑关系,特别是在接受宗教信仰的影响上所存在的相同叙事结构,使我们更容易理解美术考古和宗教美术的学科定位。
[参考文献]
[1]杨泓.美术考古半世纪[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
[2]阮荣春,主编.丝绸之路与石窟艺术[m].沈阳:辽宁美术出版社,2004.
[3]朱浒.全国首届艺术考古学理论研讨会会议综述[j].中国美术研究,2007,(3).
篇5
城市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也是历史文化的结晶与载体。无论是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文化传承绵延不绝且迄未中断的东方文明古国,还是那些在异域里抑或昙花一现抑或影响深远的古老文化,都产生或者孕育了大量瑰丽而又宏大的城市文明。而城市考古学就是让这些沉寂地下的文明重见天日,向世人再一次展现它千姿百态的历史文化的一门学科。
一、城市考古学的源起
近代考古学诞生之日起,城市考古即已成为考古学的重要内容之一。18世纪中期,对意大利庞贝古城和赫库兰尼姆古城的发掘,引起了人们对古典考古学的新兴趣,开创了世界城市考古的先河。
庞贝城是亚平宁半岛西南角坎佩尼亚地区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始建于公元前6世纪,公元79年毁于维苏威火山大爆发。庞贝城被埋没后,在其上成长出茂密的森林。后来从罗马南下和从希腊、西西里北上的移民们伐去树木之后,开始种植葡萄。公元1748年春天,一名叫安得列的农民在自家的葡萄园里发现大堆熔化、半熔化的金银首饰及古钱币。之后一批历史学家与考古专家来这里进行考古。后于1876年开始组织科学家进行有序发掘庞贝古城。经过专家的持续工作以及工作人员的辛勤维护,因火山爆发而遭埋没的庞贝古城经考古专家挖掘已大部分重见天日。
公元79年赫库兰尼姆(Herculaneum)与庞贝、斯塔比亚两城一起为维苏威火山大喷发所湮没。古城的挖掘始于1709年,1738年在遗址中挖掘出石碑,从石碑的铭文上证实,地下古城就是人们苦苦寻找的“赫库兰尼姆”。考古学家真正的对赫库兰尼姆古城的挖掘开始于1927年。赫库兰尼姆城由于被坚固熔岩所覆盖,上面又有了新的建筑,据说发掘工作困难重重几度被迫停止。
二、城市考古学的概念
以上提到这两个城市的考古,是指在考古学研究中,以古代城市为主要研究对象和工作重点的城市考古。它以古代城市的全部遗存为对象进行调查、勘探和发掘。运用各式科技手段和多学科的合力,来获取和破译考古遗存及其人文信息,努力去复原古代城市的历史和文化面貌,概括城市发展的特征,总结规律,进而探索和研究古代城市人的思想和行为的模式。而我在阅读《城市研究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Urban Studies)中所看到的关于城市考古学这一辞条的内容是有所不同的,其所指的内容与欧洲扩张所引起的城市考古学有关,它的考古对象主要指的是近代早期之后的一段时间的欧洲城市。所涵盖的内容不包括古代城市的考古,比如古典时期的雅典,罗马及其他城市,也不是文艺复兴时期和巴洛克时期的欧洲艺术,而是欧洲最引人注目也是最臭名远扬的一个创造即与殖民主义及与资本主义发展有关的城市考古。
1979年,美国人心目中的“城市考古学之父”伯特・萨尔文(Bert Salwen),对城市考古学的含义做了重要的界定。他区分了两种不同的概念;一个是“在城市中的考古”(archaeology in the city),另一个是指“城市的考古”(archaeology of the city)。前者是指对某个遗址的挖掘工作恰巧位于现代的某个城市,但是这个遗址并不一定反应这个城市中心区域的发展。另一种,即“城市的考古”,主要是指,对这个遗址的研究要与其所在的城市的历史发展相关,其考察的是这个城市的整个历程,包括它的形成与发展,并且能够从其物质性遗存(material remains)中探寻出它都市化的整个进程。
城市考古中,城市考古的对象即城市的全部遗存是极其丰富、全面的,但考古工作者所能够发掘的面积占总的遗存只是很小的比例,并且从中获取的文化信息也是有限的。所以首先要做到的是从城市的整体性去思考和把握考古工作的各个部分。要充分考虑到所考察的城市遗存形成的时间、原因以及它的形态和分布。尤其是城市作为人主要生存和不断改造的环境,考察它的各个不同区域的不同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例如,墓地在城市地区的考古工作中就非常重要。尤其是对墓地中的人的研究,他们的健康的状况以及生命的长短以及葬礼习俗都能为城市考古研究提供大量的信息。
大部分的城市的考古研究(包括中国)都主要集中在古代城市或者现代城市的更久远的历史在最近的几十年中,城市考古学家才将他们的注意力转向对于现今城市的近代历史的研究。尤其是到19世纪60、70年代,由于考古对象的专业划分,提出了“历史考古学”、“殖民地考古学”、“历史遗址考古学”、“水下考古学”等,类似我所提到的关于城市考古学的概念的界定逐渐出现,考古工作也相应地繁多起来。下面我想主要以英国为例,同时也简要介绍一下美国、中国等城市考古工作的概况。
三、国内外城市考古学的发展进程
(一)英国
伦敦,这座古老的城市,它被近两千年前的罗马人所发现,拥有最长的城市考古的传统。其实大多数的英国城市(包括伦敦城的三分之一)都在二战期间被毁坏。战争之后,这些城市大多进行重建,考古学家也就在这一时期开始了急迫的大规模的挖掘工作。20世纪40、50年代,考古学家们对伦敦城的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在最近这些年将注意力转向了中世纪后期之前的伦敦的早期历史,近代考古学的研究,尤其是后中世纪考古学是一个新的领域。
伦敦的考古与现代资本主义的传播有密切的联系。许多工业遗址都与16世纪开始的商业贸易、殖民活动有关。在对一些遗存的挖掘过程中,发现了玻璃和陶器制品,在码头和港口还有烟草制品,这些物品都是与殖民出口市场相互联系的。城市考古工作还展现了伦敦这座城市的全球影响力。2005年在伦敦泰晤士河南部的哈默史密斯挖掘出一个17世纪的砖炉,它属于尼古拉斯・克里斯普爵士的私人领地。而在十七世纪的上半叶,正是克里斯普爵士垄断了从西非几内亚到西印度群岛的奴力贸易。所以说,伦敦的城市考古发现是与英国殖民体系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密切相关的。
大多数英国的地方城镇的研究都遵循了相似的轨迹:人们对这些城市的悠久历史的拥有长时间的兴趣,而在最近几十年人们的这种浓厚的兴趣又都集中于后中世纪。例如约克郡,它拥有2000多年的历史,融合了罗马人、撒克逊人和维京人统治的多样建筑和文化。一直备受考古学关注,但直到最近对其近代城市考古研究才被接受。
(二)美国
在路易斯・宾福德的《作为人类学的考古学》中,开篇就提到有人一针见血的指出“美国的考古学就是人类学而不是其他”。二十世纪中期之前,或者说是二战之后的一段时间,大多数美国的城市考古工作都被一些业余爱好者所做。因为对于现代城市进行考古将要面临的是一系列的考古问题和技能要求。考古工作面临更多的是每个城市自身特有的状况。在挖掘过程中所需的时间长度和所使用的专业设备就需要更多的额外费用。所以,在美国,这些考古工作的业余爱好者一般拥有自己的小机构以维持他们的经济需求。业余爱好者们还要特别小心的处理与其他专业人士、商人和官员的关系。面对公众更要老练圆滑。由于得不到专业人士的帮助,甚至要培养军队,请非专业的人士提供帮助和建议。
比如说当时的威廉・卡尔弗(William Calver)与雷金纳德・博尔顿 (Reginald Bolton)开始了在上曼哈顿城的殖民遗址及独立战争遗址的挖掘。而在费城这项工作一般是通过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由专业人员完成的。还有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在本杰明・富兰克林故居及独立公园的几个遗址开始的挖掘都是这样完成的。这些挖掘都非常重要,美国的城市考古工作向考古学家们证明:在高度城市化的地区,一些关于过去历史的相关残存也是有可能幸免下来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城市都开始了类似的挖掘工程,数目繁多,并被集结成关于城市考古学的书目。
(三)中国
我国城市考古取得了很多成就,它既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同时又是拓展的难逢机遇。2012年的2月,我看到了这样一则新闻报道,在湖南,位于长沙市潮宗街万达广场的一个项目即将开工建设。在开工前,由于项目处于古城文物埋藏区内,文物部门对这一地区进行了勘测,并发现了众多古建筑遗迹。其中包括两处大型古代夯土墙体。这两处墙体尤为珍贵:分别是一号墙体,明清时期长沙城城墙;二号墙体,宋代长沙城城墙。城墙痕迹清晰可见,可以体现出来近千年来城市地层关系以及城市与湘江地理位置关系的变化,研究价值极高。现已上报国家文物局审批,等待解决方案。
在中国,许多城市都在进行开发建设,新的楼房拔地而起,老城区的纷纷被改造。这些给城市考古提供了难得的机会,但也使其面临城市遗址保护和城市翻新建设的双重问题。与其他的国家相比,我国的考古工作还存在缺乏准备,考古力量薄弱,并且考古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中国要解决城市考古的生存和发展问题,也要理清好城市考古与城市建设相矛盾的状况。另外城市考古受到的制约因素较多,尤其是被叠压在现代城市下面的古城遗存,更是难以进行考古操作的。总之,要更多的借鉴他国的成功经验,更合理的处理城市建设与城市考古之间的关系,中国的城市考古之路仍是艰辛和漫长的。
参考文献:
[1]柴尔德.安志敏、安家瑗译.考古学导论(续)[J].考古与文物,2001,(1).
[2]刘建国.城市考古学导论[J].南方文物,1995,(4).
篇6
艺术考古学研究的专业性十分明显,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艺术学的研究更加专业化,其中包含的科学技术和专业技能有许多已经超越了考古学研究的范围。《艺术考古概说》第一章详细地介绍了艺术考古学基础理论,对学科的相关研究论著进行了梳理归纳。
1978年国务院批准编撰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列出有关艺术类考古学的条目,成为中国艺术考古学科的正式提出和设立。《艺术考古概说》以《中国大百科全书》为基本理论构建,指出,由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亲自撰写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总论中,将“美术考古学”作为“考古学的一个分支”,说明美术考古学的研究方法与目的:“美术考古学是从历史学科的立场出发,把各种美术品作为实物标本,研究的目的在于复原古代的社会文化。”②之后正式列出了“美术考古学”和“音乐考古学”条目,对其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目的以及与美术史、音乐史的关系等作了规定,也成为我国明确设立“美术考古学”和“音乐考古学”专业学科的依据。作者依据上述文献,对艺术考古学的分类、主要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等进行了阐述,说明艺术考古学是探究中国古代精神文化的起源和发展,探究艺术的起源和发展规律的学科。许多艺术遗迹和遗物,凝结着古代物质文化发展的高级形态,因此艺术考古研究也是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的重要补充资料,并且涉及许多自然科学知识,是研究我国科学技术发展史的重要补充。作者除采用考古学、艺术学研究基本方法外,还特别指出运用自然科学原理和方法研究艺术考古的重要性。
二、案头・田野――研究领域新突破
在第二章至第六章的分类介绍中,作者“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取得的重大成果,作为推动艺术考古学研究的学术背景。20世纪80年代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的发掘,引起国内外关注,两个遗址挖掘清理出土大批文物,在世界尚属首次,它们的文化内涵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探究。两个大遗址的保护和利用,已被列入国家大遗址保护工程,并取得了成功经验,为四川省艺术考古的全面研究、开发、转化、利用,打下基础。例证、图片丰富,每一部分的参考文献也十分标准,可以看出,作者在前期的搜集和考证中的扎实案头工作。
我国艺术考古理论的探索实践,可追溯到20世纪初期西方科学技术和学术思想对我国学术理论界的影响,书中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创建中国美学、音乐学、甲骨学、考古学、古建筑学的奠基人的理论思想作了论述。如我国第一代美学思想家朱光潜、宗白华先生;我国第一代音乐理论家王光祈、杨荫柳先生;我国第一代考古历史学家李济、郭沫若、夏鼐、冯汉骥先生;我国第一代古建筑学家梁思成、刘敦桢、童、杨廷宝先生等。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赴西方或者日本留学后,回到中国,运用西方理论方法,研究中国古代艺术,在古物考证、文化内涵分析以及建立方法论等方面,填补了中国某项专业理论研究的空白,开启了中国美学、中国音乐史、中国考古学、中国古建筑学等理论研究之先河,中国艺术考古学的基本理论思维,也在这些专科研究过程中产生。
三、实用・前瞻――文化产业强推动
艺术考古学,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也成为艺术事业建设中快速发展的一种艺术类型。作者认为,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对艺术欣赏需求的不断增长,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不断发展,艺术考古成果的开发和转化,将成为文化艺术事业、文化创意产业的一个强势品牌,在对外文化交流活动中,在丰富国内大众文化鉴赏娱乐活动中,都会以其不可替代的独特品质,受到观众的喜爱,成为展演、影视市场上不断创新的类型。在中华文明探源研究工程中,进一步明确了人类精神文化起源。
《艺术考古概说》一书中,作者分析了目前艺术考古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如缺乏统一的综合研究机构,出土文物的调查研究受到行业管理约束,各类艺术考古所需用的科技手段如“音乐声学测量”等专业性强、技术上难度大等问题,提出了建立艺术考古学综合学科、在大学或研究机构开设专业课程、建立艺术考古研究协会等设想。在书中,作者还从打造精品品牌、推广多媒体制作和传播、规范旅游区开发、加强对外人文交流和宣传、筹建艺术考古专业六个方面,提出了针对四川地区艺术考古成果的开发与转化建议。在开发转化方面,四川落后于湖北、湖南、河南等省,归结原因是缺乏资源整合与合作开发。四川应在已有成果,如三星堆博物馆、金沙遗址博物馆等的基础上,合理利用地方考古资源和考古人才,推动四川艺术考古发展。
四、巴山・蜀水――古老文化的焕新
篇7
虽然中国音乐考古学的前身可溯至北宋以来的“金石学”,但近代学科意义上的音乐考古学当始于刘复在1930—1931年间,对故宫和天坛所藏清宫古乐器的测音研究,正是刘复将“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理想付诸于研究中国古代音乐的实践,并在此基础上所取得的一系列研究成果,才揭开了中国音乐考古学新的篇章,中国音乐考古学才得以真正“登考古学之堂,入音乐学之室”。譬如:杨荫浏在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中国音乐史纲》一书中,援引了当时许多有关出土文物的发掘资料和研究成果;李纯一搜集了大量考古发掘的古代乐器及其研究成果,并将这些成果运用到《中国古代音乐史稿(第一分册•夏商)一书中,这两位学者对考古资料的充分占有和有效地运用改变了自叶伯和以来的中国音乐史研究“从文献到文献”的旧传统,音乐考古学的作用也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
二、音乐考古学作用于他种音乐学分支学科
音乐考古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是在考古学和音乐学的羽翼下逐渐形成的。于音乐学而言,音乐考古学是音乐史学的一个分支,这也得到国内外学者一致的认识,例如,德国学者德列格将音乐学分为历史音乐学、体系音乐学、音乐民族学(民俗学)、音乐社会学和应用音乐学五大类,其中,音乐考古学是作为历史音乐学的一个部门而存在的;音乐史学家李纯一认为:“它(音乐考古学)应该既是普通考古学的一个特殊分支,又是古代音乐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虽然音乐考古学是历史音乐学的一个分支,但其在整个音乐学体系中的地位却并非仅仅只作用于音乐史学的研究,其对中国古代音乐美学史,以及当下的民族音乐学的研究依然有着促进作用。
三、音乐考古学作用于音乐史学
较之于其他音乐学科而言,音乐考古学与音乐史学的关系尤为密切,这是因为:其一,在研究对象的时间维度上,它们都是指向于过去,研究历史上的音乐事项,以了解古代的音乐社会生活;其二,在史前史时期,音乐考古学研究是音乐史学研究的主要手段,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出现之后,有关音乐的考古实物和文献典籍是音乐史研究的两大史料来源。具体来说,音乐考古学对音乐史学的作用大致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考古史料可以弥补文献的不足
人类发展的历史是极其漫长的,即便是从旧石器时代算起,也大约有300万年的历史;而人类用文字记载的历史,也就是说有比较确切的资料可以证明的信史,就中国而言,大约是从公元前17世纪的商代开始的,距今不过4000年左右。从300万年前到4000年前,这么漫长的历史,除了通过神话传说获得一鳞半爪的模糊的认识之外,我们几乎一无所知。如《吕氏春秋•古乐篇》载:“帝尧立,乃命质为乐。质乃效山林溪谷之音以歌。”《山海经•大荒西经》载:“开(夏后启)上三嫔于天,得《九辨》《九歌》以下,……开焉得始歌《九招》”等等。通过这些记载认识商以前的历史不仅模糊不清、无法得以考证,而且也是一种无奈。可见,通过文字了解人类音乐的历史,其局限性不言而喻。而大量考古出土的音乐实物以及对它们所进行的科学研究,不仅改变了我们对史前音乐历史的了解主要依靠神话传说的尴尬局面,也改变了我们对史前音乐历史的认识。例如,1987年,河南舞阳县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25支骨笛,据碳14测定和树轮校正,距今约8000—9000年;根据测音和实际的演奏实验表明,这些音已包括了六声音阶和七声音阶,并且可以吹奏较为复杂的曲调。这一结果不仅改变了我们之前对新石器时期音乐认识上的空白,而且也改变了对已有的中国古代音乐诸多研究成果的认识,促使我们对其进行重新考量,如学界很长一段时期都在争论的“战国时期有无五声音阶以外的偏音”的问题;音阶发展史是由少渐多,还是一个从多到少不断规范的过程的问题等。这方面的音乐考古发现甚多,如浙江余姚河姆渡骨哨、西安半坡陶埙等。可以说,从科学的意义上研究史前音乐历史,考古实物是唯一的途径和手段。它不仅是我们了解史前音乐历史的不二法门,也对其后有文字记载的音乐历史的研究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2.考古史料和文献互证
考古史料和文献史料互证,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源于20世纪20年代王国维对古代历史的研究。他主张研究古史当以地下史料参订文献史料,这在历史学界有很大的影响,这种研究方法被学界称之为“二重证据法”。“二重证据法”的提出,一方面导源于对科学研究实证精神的追求,另一方面则是考古学在中国的不断发展与成熟。这一研究方法对研究中国古代音乐史也有很大的影响和促进作用。王光祈在其《中国音乐史》一书就曾指出:“研究古代历史,当以‘实物’为重,‘典籍’次之,‘类推’又次之。”[2]其后,学者们都自觉和不自觉地将此方法运用到研究中国古代音乐史的实践中,中国古代音乐史的研究面貌也因此为之一变,它不仅改变了传统史学“从文献到文献”的旧传统,也使研究所得之结论多了些许的实证面貌。例如,古书中有关鼍鼓的记载甚多,《吕氏春秋•古乐篇》:“帝颛顼令鱓先为乐倡,鱓乃偃浸,以其尾鼓其腹,其音英,即鼉也”、《诗经•大雅》:“鼍鼓逢逢,矇瞍奏公”、李斯《谏逐客书》和司马相如的《子虚赋》提到的“灵鼍之鼓”。鳄鱼在古代被称作鼍,鼍鼓即是用鳄鱼皮制作的鼓。在没有有关鼍鼓的文物出土之前,学界对这些记载多半持将信将疑的态度,但1978—1980年山西襄汾陶寺遗址3015号大墓木鼍鼓的出土,释解了人们心中的疑团,从而确信鼍鼓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的真实存在。
3.匡正用文献研究可能出现的谬误
翻开历朝历代正史乐志可知,其中有关音乐的记载多出于统治阶级之手,所载内容侧重于宫廷雅乐,对宫廷之外丰富多彩的民间音乐记之甚少,有些御用文人为了取悦于统治者甚至会歪曲历史,因而必然有阶级的和时代的局限性;此外,在“重道轻器”的古代,记载音乐之人往往都不是具有音乐专业知识的乐工,而是一些对音乐一知半解的文人,这也必然会使有关音乐的记述含混不清,乃至错误失实,以讹传讹,贻害千年。如此,考证、校雠等传统的研究方法一筹莫展,考古史料则表现出其特有的参证和纠错的作用。这方面的典型事例以曾侯乙墓乐器的出土为要,1978年,曾侯乙墓的发掘及其大量精美的乐器的出土不仅向世人展示了一个“地下音乐宫殿”的辉煌,其重大的意义在于改变了我们对已有的通过文献研究而获得的中国古代音乐史一些偏颇的认识:其一,对一钟双音现象作了最充分有力的注脚。1977年,吕骥、黄翔鹏等音乐家去甘肃、山西、陕西、河南四省做音乐考古调查研究时,发现了中国古代的钟,在敲击钟的不同位置时可发两个相距三度的音,但这一理论在提出时遭当时学界众多人的怀疑,人们普遍持否定态度。次年,曾侯乙墓编钟的出土,让世人承认并接受了“一钟双音”的事实。其二,对于中国古代音乐史上一直争论不休的“古音阶”和“新音阶”的问题。其三,对于中国只有首调唱名法而没有固定调唱名法的问题以及工尺谱的渊源、中国的乐律学理论等诸多有争议的问题都作了很好地解释。
4.扭转了用文字描述音乐史非直观形象的不足
音乐是一门时间艺术,也是一门声音的艺术。撰写一部有声的中国古代音乐史一直是音乐史学家的追求,从杨荫浏“音乐史是不能没有音乐的历史”[3]的治史观到黄翔鹏“曲调考证”研究的身体力行,无数学人为此孜孜不倦地摸索着;但我们同时也应知道,音乐生活的画面并非仅有声音组成,在三维空间里尚有乐器的形制、乐队的组织、器乐的编排以及乐人的服饰和奏乐的场景等,考古出土的遗迹、乐器实物以及音乐图像,包括绘画、画像砖、编织图、乐舞俑、洞窟壁画、器皿饰绘、墓葬壁画、画像石、石刻、书谱等,则可以直观地以立体的或平面的方式完整地再现历史上的音乐画面。例如,文献中有关先秦瑟的形制的记载语焉不详,甚至有分歧之处,我们如若仅仅通过文献并不能对此有清楚明白的了解。但湖北、湖南、河南等地古墓出土的有关先秦瑟的实物,则能立即给予我们非常明确的感官认识:先秦瑟的形制是“四枘四岳”式,一般具有二十三至二十五弦和柱。所谓“百闻不如一见”!再如,李荣有《汉画像的音乐学研究》一书通过对大量出土的汉画像石的研究,揭示出了汉朝音乐生活的诸多层面;《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收集了各省的出土器物,形象而直观地展示出了各地区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出现的乐器的类型、特征等,并可以对不同省的出土乐器进行比照,揭示其间的异同之处和源流动向。可以说,考古史料让音乐史的研究具有了现场感和亲切感,让人如置身于历史的语境之中。
综上可知,音乐考古学虽然是考古学和音乐学的交叉学科,其下属于历史音乐学,但其在整个音乐学学科体系中的作用,并非仅仅局限于音乐史学,其对于拓宽和延展音乐美学的研究对象,丰富音乐美学的研究内容;对于改变民族音乐学在研究少数民族音乐研究时文献史料不足的局面,全面深刻地阐释音乐背后的文化意蕴等都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作者:于珊珊 单位:西华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篇8
音乐考古学研究的方法论架构
在所有已提出的音乐考古学研究范式中,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受到推崇(14)。大家均赞同,音乐考古学由一系列多学科的方法或分析模式所组成,其具体方法则由研究主题所依赖的资料所构成。如前所述,这些研究资料具有多样性,它包括与音乐相关的发现和涉及音乐的历史记载,有时甚至是依然存活的音乐传统。由人类过去的遗物可知,这些资料在类型和内容方面均存在个体差异。重要的是,为获得实证性的结果,所有资料均应考虑以互补的方式加以比较。换句话说,这些资料均应予以同等对待。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种方法的有效性已经得到许多研究的证明。分析方法的多样性还表明,最佳的研究结果乃由不同领域的专家组成的研究团队所获得。
已有的研究范式显示,音乐考古学的具体研究方法会有所不同,这主要基于应用的资料和分析的模式。在研究的总体目标上,可从音乐知识(包括“文化知识”、“乐器学知识”、“律学知识”等等)(15)到文化/自然的声音(16),也可从音乐表演(17)到音乐文化(18)。根据音乐考古学研究的一般范式(见下文),以及上述音乐考古学的定义,我将研究的总体目标界定为过去的音乐行为和声音。
研究方法的主要差异,体现在音乐考古学家和民族音乐学家对过去的音乐所持有的不同观点,后者已经在20世纪60年代由Merriam予以阐述(19),随之由Blacking(20)、Nettl(21)和Mendívil(22)等人做过进一步探讨。虽然大多数音乐考古学家倾向于研究过去的音乐行为和声音,包括与依然存活的音乐文化做比较,但后者仅作为一种辅助的研究方法。民族音乐学家虽然对考古和历史问题感兴趣,但更倾向于研究现状并探寻其中尚存的过去的踪迹,从而将历史科学作为辅助的研究方法。两者的出发点都是有价值的,且并不互相排斥,但对其交互关系的探究目前则所见不多(见下文)。
如果将现存的所有资料和重要的分析模式加以整合,即可形成一种普遍适用的音乐考古学研究的方法范式。这可用一般的范式来表示(见图),并可作为世界范围内个体研究的结构框架。这个范式由两个同心圆围绕总体目标构成,其中所有的部分均可作为独立研究的课题。外圈联结着四组音乐考古材料(发声器、音乐图像、音乐文献资料以及存活着的音乐传统),内圈是一些主要的学科,分析模式通常即从中产生(音响学、乐器学、考古学、音乐图像学、民族音乐学、民族历史学和文献学)。
音乐文献资料 文献学 音响学 发声器 乐器学 民族历史学 过去的音乐行为和声音 考古学 音乐图像 存活的音乐传统 民族音乐学 音乐图像学
J52Y401.JPG
图 音乐考古学研究的一般范式
由于研究材料的情况各自不同,因此音乐考古学研究的结果也具有不同的意义,重要的是每种方法要针对不同的个案研究。最为全面的研究结果只能在每项资料具有足够的信息时才能获得(23),这意味着音乐考古学研究的成功更多依赖的是特殊的原始资料及其互补性。材料经常是残缺不全的,但也要作为研究的课题,因此以一种或几种方法去处理它们通常是不够用的。音乐传统的年代越久远,研究就会变得越困难;文献资料越丰富,探索其原貌的基础就会越好(24)。因此,音乐考古学研究和阐释的可能性确实是十分有限的,在涉及到非常遥远的、仅遗留有极少物质资料的音乐文化时尤其如此。
音乐考古学研究与民族音乐学
比较音乐学作为民族音乐学的前身,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就已出现。十分显然,它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历史科学(25)。除了方法的不同以及后来受到严厉批评的假设和臆断之外,它与音乐考古学具有一些共同的研究目标。在研究的课题领域中,比较音乐学家重视音乐的起源,他们认为这在当今所谓的原始文化中可以进行考察,并可从单线进化朝着“文明的”方向来分析音阶构成和乐调体系(26)。20世纪60年代早期,作为新研究方法的一部分,历史问题包含其中,民族音乐学被视为音乐人类学(Alan Merriam),重点研究音乐在社会中所产生的作用。在音乐与文化史一章中,Merriam指出,要通过音乐和乐器研究重建文化史(27),这是民族音乐学研究的组成部分。对于历史科学如考古学和民族历史学的研究目标来说,这样的研究方法也是有价值的。
Merriam之后的学者,例如Blacking和其他人,都提出特殊的音乐和社会形态是特定文化认知过程的产物,在音乐的行为方式和社会组织之间具有牢固的联系。根据这种理解,音乐文化依赖于人类组织和声音模式,声音的生成是有组织的相互作用的结果(28)。Blacking认为,民族音乐学的目标是研究文化结构及其音乐之间的关系,并认为文化与人为组织起来的声音是相互依存的。近来推断,对音乐结构的社会文化关联性的探索并未取得太多的成功(29)。然而,不能否认研究文化样式与音乐之间关系的重要性,因为音乐从未与它的创造者的个人经验相脱离,音乐的创造者深入地参与到广阔的文化和历史进程之中(30)。
当探索民族音乐学对音乐考古学的适用性时(31),两个学科间的一项重要结构差异便显现出来。音乐考古学最明显的矛盾是,截止近代(以1877年留声机的发明为转折点),过去的所有音乐都消失了。然而,音响考古学研究并非不可能,一些研究表明,这个矛盾至少能部分得以解决。不同的文化产生不同的乐谱形式,它们很难被解读,但至少一部分能被破译(多数例子与美索不达米亚、古希腊和古罗马有关)。文献资料也为我们提供了仪式歌曲和圣咏的文本;在古文字和其他历史文献中,表演实践、演奏技术乃至音响风格都是相互关联的(从不同程度的主位与客位角度观察)。现存的描述显示了乐器的种类和特有的演奏姿态(遵循着不同的艺术习俗和规则),乐器的发现至少能帮助我们重建创作音乐的构成元素(例如基音频率、和声、音色和音程等的可能性)。然而,即使拥有大量的音乐考古材料,结果仍是有限的,因为在大多情况下,过去的音乐在节奏和旋律结构方面均超出了科学研究的范围(见下节)。
另一方面,音乐表演和与其产生相互作用的社会文化语境,在民族音乐学和音乐考古学中都是熟知的研究课题。事实上,有时会有丰富的研究材料。从有关音乐发现的考古学背景,到大量的图像和文献记载,使我们更多地了解过去的音乐文化。在这种情形下,作为研究课题,由于资料的完整性和零散性各异,会导致研究方法的不尽一致,但从研究目标来看,音乐考古学和民族音乐学是一致的。就音乐考古学而言,在将过去音乐行为的社会文化面貌呈现在面前的同时,过去的声音只有在某些方面能够得到复原。
民族考古学和实验考古学
20世纪60年代早期,传统考古学受到所谓新考古学的挑战,新考古学所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传统考古学将出土文物的描述作为主要的研究目标。Binford和其他人转向人类的行为和文化模式,将物质文化的解释作为一种考察手段,而不是局限于物质的形态范围(32)。从考古人类学(Lewis Binford)引发的问题,关注考古学人工制品的生产技术以及它们的特定社会文化功能。即便没有进行过充分的讨论,但这种方法对音乐考古学研究的适用性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得到公认(33)。依我来看,新考古学有两种方法对于古代声音和音乐行为的研究至关重要,即:民族考古学和实验考古学。
民族考古学
如果将考古资料与民族志资料的比较作为有价值的研究工具,那么民族考古学则是通过对当今民族事象的研究,来了解过去的文化样式。Hodder定义了两种不同的研究类型:考古学与民族志器物如各种工具的形制比较(关系类比);过去与当今技术处理相似性的比较(形式类比)(34)。在民族考古学中常用的方法是直接历史研究法,当具备历史和文化的连续性条件时,直接比较便成为可能,而一般比较法则无需这样的链接即可构建其相似性(35)。当对不同文化资料的解释做多样性考察时(36),应用民族志类比方法来理解考古资料的主观风险便可降低。
民族志类比方法对音乐考古发现的解释相当重要,这说明它与民族音乐学研究关系密切。确实,民族考古学的方法可以作为音乐考古学与民族音乐学之间的桥梁,但在探索它们的交叉性方面,目前所获经验并不多。直接历史研究法在众多个案研究中得以应用,如西班牙统治前的美洲音乐文化与当今美洲土著音乐传统的比较(37)。但间接的比较也是有用的,尤其是狩猎采集社会与史前音乐文化的比较(38)。
尽管音乐考古学的解释有其优长,但与后世时间跨度较大的文化做比较研究仍然面临相当大的困难。对音乐传统做时间跨度和历史深度的考察,在音乐考古学和民族音乐学中是最具挑战性的分析研究。更为复杂的问题是,我们对过去的认识常常是静态的,音乐考古学的解释反映出这种问题,在原始材料不足时尤其如此(39)。少量乐器或图像的发现,并不一定代表一种特定的音乐文化,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中,由于文化内部和跨文化之间长久的交互作用,文化本身也会发生变化。不过,即使像乐器那样的器具,在很长的时间 内可能会保留它们的形态,且很可能被吸收和植入新的环境之中,因此会有不同的、甚至是相互对立的功能和意义。一种特定的乐器形制可以传留数千年时间,如东亚的琴筝类乐器和东南亚的弓形竖琴。但用这些乐器演奏的特定音乐以及特定的表演背景和含义,均可能发生相当程度的变化。在追索音乐传统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中,对文献和图像资料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在关注过去音乐的社会文化背景和意义方面尤其如此。
实验考古学
实验考古学研究旨在运用复原和重建古代生活样式的手段,并通过与过去的比较,来从事考古学研究(40)。与民族考古学方法相比,它基本上不是诠释他者(如依然存活的原住民文化);相反,考古学家转而成为行为人,通过他或她自己的切身体验,来比较实验的价值。在被称为模拟实验的方法中,研究者发现了一系列与过去的经验类似的技术变革。常见的研究课题是,使用原始工具和技术对考古发掘物进行实验性的复制。对古器物使用方式的重建即其显例,如旧石器时代的燧石工具,能够发出与劳动相关的特殊而有节奏的声音。一些燧石拥有动听的石制板体乐器的音响,即使它们不具备音乐功能,但在过去至少应会引起人们的注意。
显然,实验考古学的方法在音乐考古学研究中是适用的。有关音乐考古发现的乐器学和声学研究已经超过一个世纪,如今在音乐考古学中更是必不可缺。有两种分析方法最为常见:第一,复制品和“仿真模型”的实验性制造;第二,复制品的实验性演奏,或如果可能的话,演奏发声器原器。这两种方法是密切相关的,因为发声器的实验性复原,往往是实验性演奏的前提。实验音乐考古学的研究,通常是与乐器制造商和音乐家共同合作来实现的。
实验制作过程提供了精确的乐器学信息,其所需前提条件往往是对制作材料的分析,包括对材料的产地、处理以及工艺的考虑,常使用直接目测观察和考古测量的方法(光谱学、X光照像技术、材料研究,等等)。这些分析还提供了制造的特殊信息和古代加工材料的知识,以及制造完成后乐器的操作乃至演奏痕迹。此外,也能够了解乐器独特的声学原理。实验方法还可通过仿真模型得以实现,即根据特定的研究对象,不必使用原材料来复制乐器(如气鸣乐器)。
对古乐器或其复制品的试奏,能够考察乐器的演奏技巧,并能显示特定乐器的音响性能(若几种乐器发现于同一考古环境当中,或图像中描绘的是一组乐器,就要考虑它是独奏或合奏所用)。发声器在保存状况较好且可演奏的条件下(如陶响器、陶笛、螺号、陶号、石制板体乐器,等等)可以用作实验研究,而乐器残品以及不宜演奏的乐器(如古代弦乐器)则需以复制品来进行实验研究。与此相关的是音响空间和音响性能的研究,其中声学模化软件和3D应用程序也被应用。
如上所述,演奏姿势和技巧以及出土乐器的声音特性,都能通过实验来加以重建和检测。当涉及气鸣乐器(例如带指孔的骨笛、排箫或螺号)以及成套的体鸣乐器(如编磬和编钟)时,重建其音列也是可能的。然而,实验性的演奏在音乐考古学中属于最困难的研究方式,因为我们往往并不掌握过去音乐的特殊结构及其重要信息。再者,虽然文献与图像资料的有关信息有一定价值,但即使在演奏姿势方面,从特定发声器的人体生理学角度看,也会限制其演奏技巧和声学性能,因此其真实性存在较大的差距。以笛子为例,实验性演奏的结果不能视为特定音阶或调式的证据,因为不是所有的指孔可以均等地使用,并且还可通过呼吸控制技术以及指孔的部分闭合等来改变音响(41)。例如,如果只是给出乐器尺八(同上),人们可能完全不晓得日本尺八音乐,这同样也适用于旧石器时代由禽鸟骨和猛犸象牙制造的笛子,这只不过是采用了最早的考古学案例而已。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可以在复制品上奏出与公元前33000年乐器同样优美的旋律。事实上,正如Nettl用一些显著的例子所论证的那样(42),重建古代音阶体系以及其它音乐构成要素,仍然带有很大的推测成份。只要有相当数量的考古材料,即可通过定量分析,来帮助获得验证的结果。然而,在大多情况下,发声器的声学研究并不能揭示出过去音乐的旋律和节奏方面的足够信息。在声音的再现技术产生之前,过去音乐的音响全都消失殆尽。
以往何时、如何以及为什么制造乐器并用来发音的问题,较之过去音乐的构成问题,在音乐考古学中会起到更大的作用。前述科学研究中的局限,属于科学与艺术结合的臆测或即兴发挥。显然,这样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出于研究者或音乐家的想象,它相当于对音乐史的艺术化阐释,只是简单反映了目前我们对过去音乐的看法。
本文译自Arnd Adje Both. "Music Archaeology: Some Methodological and Theoretical Considerations." Yearbook for Traditional Music 2009(41): 1-11.
收稿日期:2013-10-12
注释:
①我基本采用两个早期的释义:“通过古物遗存研究作为文化的音乐”(Olsen 1990: 175),“古代声音和音乐行为的考古学”(Lawson 2004: 61)。
②Blacking, John. "Ethnomusicology and Prehistoric Music Making." In Hickmann, Ellen, and David W. Hughes. Ed. The Archaeology of Early Music Cultures: 3rd International Meeting of the ICTM Study Group on Music Archaeology. 330-331. Bonn: Verlag für Systematische Musikwissenschaft, 1988.
③Both, Arnd Adje. "Aztec Music Culture." In "Music Archaeology: Mesoamerica," ed. special issue, The World of Music 2007(49)/2: 91-104.
④原文为:archaeology of sound,译者注。
⑤原文为:sound archaeology,译者注。
⑥原文为:music archaeology,译者注。
⑦原文为:archaeomusicology,译者注。
⑧Hickmann, Ellen. Aims, Problems and Terminology: Current Research in European Archaeomusicology. Ed. Graeme Lawson. Cambridge Music-Archaeological Reports, 6, Cambridge, 1983; Vendrix, Philippe. "Archéo-musicologie ou musico-archéologie." In Otte, Marcel. Ed. Sons originelles: Préhistoire de la musique. 7-10. Liège: Université de Liège, 1994.
⑨Megaw, J. V. S. "Problems and Non-Problems in Palaeo-Organolo gy: A Musical Miscellany." In Studies in Ancient Europe: Essays Presented to Stuart Piggott, ed. J. M. Coles and D. D. A. Simpson, 333-58, Leicester, 1968.
篇9
早在先秦时期,即出现了“百家言黄帝”的局面,自汉代司马迁“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择其言优雅者”作《史记·五帝本纪》以来,中国上古史研究经历了信古、疑古到考古这样一条漫长而曲折的道路。
司马迁建立了“五帝”的上古史体系后,后世多认为信史,把黄帝时代看作中国上古史的开端,并把黄帝或炎黄二帝看作是华夏的人文始祖。一方面,这种民族与文化的认同感形成了极强的凝聚力,在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另一方面,由于历代添加甚或虚构而“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也使治上古史的学者们产生了许多困惑和怀疑。于是20世纪20年代,疑古思潮盛行,认为东周以前无信史,主张“宁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然而正如中国考古学的创始人李济先生指出的,“这段思想十分混乱的时期也不是没有产生任何社会价值,至少它催生了中国的考古学”。正是考古学的出现开辟了认识上古史的新途径,才为解开中国史前史之谜找到了一把钥匙。中国上古史的研究经历了信古、疑古,最后走向考古。
从20世纪20年代中国考古学的诞生起,经过几代考古学家们数十年的发掘和研究,获得了大量的前所未有的考古资料,中国的史前文化和三代文明,在考古学家的锄头下逐渐显现出来;人类的起源、农业的起源、文明的起源这些重大的学术问题也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就炎黄文化研究而言,“考古发现已日益清晰地揭示出古史传说中‘五帝’活动的背景,为复原传说时代的历史提供了条件”。人们认识到,只有把文献资料与考古资料乃至其他学科的资料结合起来,相互印证,才是重建中国上古史、研究炎黄文化的正确道路。
然而,“对古史的怀疑与对古史的重建是二十世纪中国古史研究的最主要的两种思潮,这两种思潮不但贯穿于二十世纪的始终而且将波及下个世纪。”因此,对中国上古史和炎黄文化的研究历程的回顾与总结,是十分必要的,但实际上,笔者并没有能力对数十年来炎黄文化的研究做一个全面的总结,只能从考古学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历程做简略的回顾与思考,企望能对今后的研究有所促进。
二、炎黄文化研究的回顾
(一)20世纪50年代以前
20世纪前期,考古发现对中国上古史研究的最大影响,是“用地底下掘出的史料,慢慢地拉长东周以前的古史”。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殷墟甲骨卜辞和敦煌汉简等的发现开始,学者们就开始尝试将地下材料与文献材料相结合研究古史。特别是王国维利用甲骨材料撰写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证实了《史记·殷本纪》记载殷商世系基本可靠,进而建立了“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的二重证据法。由殷墟甲骨发现而引发的殷墟考古发掘和一系列新发现,则进一步把殷商史建立在无可置疑的实物证据基础之上。
20世纪20年代中国史前考古的一系列新发现,则把中国境内有人类的历史追溯得更为古远。1920年法国学者桑志华在甘肃庆阳首次发现了旧石器;1921年在北京周口店发现了猿人牙齿化石,同年在河南渑池发掘了仰韶村遗址进而确立了仰韶文化;1922年在内蒙古河套地区发现了“河套人”化石和石器;1928年在山东章丘县龙山镇发现了龙山文化。这些考古新发现、特别是北京猿人化石的发现,使学术界认识到,中国有^、类及其文化的历史已很古远了。
新的发现改变了上古史茫昧无稽的疑古观点,一些学者开始尝试利用考古资料并结合古代文献来探索中国古史。如徐中舒先生根据当时所发现的仰韶文化的分布地域及其文化特征,结合文献记载的夏部族的活动地域,认为“从许多传说较可靠的方面推测,仰韶似为虞夏民族遗址”。而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东、西对立分布似乎为当时颇为流行的“夷夏东西说”提供了依据。特别是徐旭生先生,20世纪30年代在陕西渭水流域调查时,曾发现了西安米家崖、宝鸡姜城堡等新石器时代遗址,并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中将传说时代的部族分为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集团,认为“炎帝氏族的发祥地在今陕西境内渭水上游一带”,“黄帝氏族的发祥地大约在今陕西的北部”。
但新的考古发现对古史传说时代的研究而言,旧石器时代的古人类化石及石器的发现,虽然证明中国在距今数十万年前的远古时期就有人类生活、居住,但这些文化与传说时代或炎黄时期相距太远。新石器时代大约相当于传说时期,“尤其是仰韶、龙山两大系文化同传说时代的古氏族的关系一定很密切。但关系的详细情形如何及如何地变化,我们一直到现在还是几乎毫无所知。我们也不敢捕风捉影地去附会,所以暂时也还不能谈。”当时的考古学家们对炎黄文化的研究大都挣慎重的态度。
(二)20世纪50—80年代
20世纪50年代以来,大量的考古发现不断拓展着人们的视野,学者们相信:“很古时代的传说总有它历史方面的素质,核心,并不是向壁虚造的。”一些考古学家们开始自觉地将考古发现和历史文献相结合来研究上古史。随着考古发现确立了夏、商文化,中国文明起源问题成为上古史研究的重要课题,而文明起源的探索又必然涉及到夏以前的“五帝”时期。因此考古学界关于炎黄文化的研究多与文明起源的研究相关联。
20世纪50年代,石兴邦先生主持发掘了著名的西安半坡遗址,使学术界对仰韶文化内涵有了更多的了解。安志敏先生在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发现的由仰韶文化向龙山文化过渡的中间环节——庙底沟二期文化,初步建立了中原地区从仰韶文化到龙山时期的史前文化连续发展的体系。这些发现使学者们似乎看到了从仰韶文化经龙山文化到夏商周文化的一元发展轨迹,而在这一过程中,中原地区是中国文明发生地和演进的中心。这样,一个祖先——黄帝,一条母亲河——黄河,一个中心——中原地区就构成了“中原中心论”的主体认识,并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而当时已知最早的仰韶文化自然被看成是中国文明的源头,并与“黄帝文化”相关联。如范文澜先生认为:“仰韶文化所在地,当是黄帝族的文化遗址。”
1959年,徐旭生先生依据文献“伊洛竭而夏亡”(《国语·周语上》)的记载,来到豫西寻找“夏墟”,并在偃师二里头遗址找到了一种晚于龙山时代而早于商代的考古学文化。以后的多次调查、发掘表明,二里头遗址是一处面积超过300万平方米,由大
型宫殿式建筑和围墙、高等级的墓葬、青铜器和玉器构成的复杂社会的遗存,它广泛分布于文献记载的夏人活动范围——豫西和晋西南。大多数考古学家倾向于二里头文化属于文献记载中的夏文化,二里头遗址应是夏代的都城。二里头文化的发现,使得从仰韶时期,经龙山时代到夏商,形成了一个文化连续发展的链条,初步显现了由史前文化到夏文明出现的轨迹,从而揭开了考古学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序幕。
20世纪60年代,随着考古资料、特别是史前考古资料的增多,考古学家们已不满足于证史或补史,而是寻求解决如何重建中国的上古史问题。李济先生指出:“现代中国考古学家的工作,不能仅限于找寻证据以重现中国过去的光辉,其更重要的责任,毋宁说是回答那些以前历史家所含混解释的、却在近代科学影响下酝酿出的一些问题。这样产生的问题属于两类,但两者却息息相关。其一是有关中华民族的原始及其形成,其二为有关中国文明的性质及其成长。”之后,如何重建中国的上古史问题,成为史学界的一个重要学术课题。
20世纪70年代,在河南登封王城岗发现了一座距今4 000年以前的龙山时期古城址,安金槐先生提出的王城岗城址即文献记载的“禹都阳城”的观点,引起了学术界极大的关注和讨论。这一发现为探索夏文化的起源提供了线索,客观上把夏文化与史前文化联系起来。不久,在山西襄汾陶寺找到了比“禹都阳城”更早的陶寺文化,先后发掘清理了上千座墓葬,其中大型墓随葬有石馨、鼍鼓、彩绘龙盘、玉钺、玉琮等分礼乐器,还出土了1件铃形铜器。晋西南向有“夏墟”之称,先秦文献有“封唐叔于夏墟”(《左传·定公四年》)的记载。因此,有学者认为活跃于“夏墟”,以龙为族徽、名号的陶寺类型文化,应是探索夏文化源头的重要线索之一。也有的学者认为,陶寺遗址当为陶唐氏尧部落中心的所在。
(三)20世纪80年代以来
20世纪80年代以来,农业考古的新进展和新石器时代初期陶器的发现,使得中国新石器时代开始的时间推进到距今10 000年前后;聚落考古在探索史前居民的社会组织结构及其演变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环境考古则为探索文明起源的外部条件提供了许多新资料。在这些发现与研究的基础上,文明起源的理论与研究方法也不断发展,促使相关学术研究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首先,考古学和文明起源理论有了较快的发展。1981年,苏秉琦先生提出“区系类型理论”,把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分为6个区系。而这一文化时空分布格局表明,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有着多个区域演化中心,于是传统的中国文明起源“一元论”或“中原中心论”受到了挑战。苏秉琦先生指出:“中国古代文化是多源的,它的发展并不是一条线贯彻始终,而是多条线互有交错的网络系统,但又有主有次。各大文化区系既相对稳定,又不是封闭的。通过区内外诸考古学文化的交汇、撞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通过不断地组合、重组,得到不断更新,萌发出蓬勃生机,并最终殊途同归,趋于融合。”张光直先生也指出:“中原文化只是这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它有它自己的历史,也有它作为大系统中一部分的历史,即影响其他文化与接受其他文化的历史。”当然,在强调中国文明起源的多元性的同时,并不能完全否认中原地区在文明起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严文明先生认为:“由于中原在地理位置上处在各文化中心区的中间,易于接受周围中文化区的先进成分,在相互作用和促进下最先进入文明社会,从而成为这种多元一体结构的核心。”这样,“多元一体”文明起源观点逐渐成为学术界的主流认识。
其次,文明与社会演进过程的研究受到普遍的重视,提出或借鉴了多种社会发展理论与模式。1983年,张光直先生首次将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塞维斯(elman serrice)的人类社会演进由游团一部落一酋邦一国家的4个阶段构成的模式介绍到中国,并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阶段进行了初步研究,认为龙山时代属由平等社会向国家过渡的酋邦阶段。之后,所谓的“酋邦理论”受到国内一部分学者的重视,并开展了相关的研究。1986年,苏秉琦先生提出了“古文化一古城一古国”的文明起源过程三阶段模式,古文化指原始文化,古城指城乡最初分化意义上的城和镇,古国则指高于部落之上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严文明先生认为:依据相关文献记述,“五帝时代是一个普遍筑城建国的时代,这恰恰与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相合”。中国古代把城叫做国,城外的乡村叫野,包括城乡的政治实体有时也叫邦。如果套用酋邦的说法,龙山时代似乎相当于酋邦阶段,但“我主张先不要硬套,就用中国古代习用的名称叫国。因为这时期的国刚刚从部落社会中脱胎出来,还保留浓厚的部落社会印记。为了跟后来比较成熟形态的国家相区别,可以称为原始国家或古国,代表中国古代文明的黎明时期。”进而提出古国(龙山时代)一王国(夏商周三代)一帝国(秦至清)的文明起源与发展三阶段模式。
再次,20世纪80年代以来,史前考古的新发现、特别是龙山时代大量的城址、铜器和陶文等发现,为中国文明的起源“多元一体”的理论提供了许多新证据。就炎黄文化研究而言,“考古发现已日益清晰地揭示出古史传说中‘五帝’活动的背景,为复原传说时代的历史提供了条件。在黄河上游齐家文化出土了许多铜器,有铜锥、铜刀、铜钻头、铜凿、铜环、空首斧、铜镜等,这些铜器有锻造,也有单范铸造的。有学者认为,中原地区铜器的出现与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有一定的关系。黄河中下游地区发现有许多城址,其中在陶寺遗址新发现了陶寺文化是、中期城址,中期的大城面积达280万平方米,特别是在一件陶扁壶残片上有朱书似“文”和“易”字的陶文。此外,在山东邹平丁公遗址也发现—块刻有11个字y的陶片。这些发现为探索文明和文字的起源提供了重要资料。在长江下游,发现有瑶山、反山等高规格的祭坛墓地和以莫角山巨型夯土台基为中心的城址,面积达290万平方米。在长江中游,发现面积达120万平方米的湖北天门石家河城址,出土了数以千计的陶塑动物。严文明先生指出:“这个时代确实是处处闪耀着文明的火花,对于后世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这样的时代自然会长期为人们所怀念,宜乎后人把黄帝推崇为人文始祖。”因此“把龙山时代同传说中的五帝时代相比照,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甚至有学者主张将这一时期称为“五帝时代”,认为“惟有称为五帝时代,才能恰如其分地表现中国古代的历史实际和这一阶段的时代本质”。
三、炎黄文化研究的思考
20世纪20年代以来、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考古学发现与研究的进程,包括炎黄文化研究在内的上古史和文明起源的探索不断取得新的成果,推动这一课题研究不断向更高、更深的层次发展,但我们还应看到,这一领域的研究也还存在着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
首先,炎黄文化应属中国上古史(或史前史)和
文明起源研究的一部分内容。张岂之先生指出:“我们研究中国文化的源头,研究先秦时期原创性文化,都需要和中国文明起源的大课题相联系。”依据“多元一体”的理论,炎黄文化仅是史前诸多文化中的一支,尽管这一支文化在文明起源过程中可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炎黄文化本身的形成乃至文明的起源,应是多种文化相互碰撞、交流、融合的结果,故探索炎黄文化的同时,也要注意研究其他文化及与炎黄文化的关系研究。因此,研究炎黄文化应将其纳入中国上古史和文明起源研究的体系之中,在“多元一体”的框架内,首先努力从考古学文化的内涵分析来探讨传说时代或“炎黄文化”的历史面貌,探索炎黄文化的形成及基本特征,炎黄文化的发展直至文明的出现等。但目前,史学界仍有部分学者忽视“五帝”时期文化多元不平衡的发展过程,对古代传说和记载又不加检视地应用,热衷用文献附会考古发现或者用考古发现附会文献,甚至直接将考古发现与古史传说中某些人物或事件对号入座。这类研究显然是不可取的。
其次,包括炎黄文化在内的中国上古史(或史前史)重建,应建立在多学科综合研究的基础之上,需要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乃至现代科学技术的参与协作。早在20世纪60年代,李济先生在《再谈中国上古史的重建问题》中指出:“我们讲现代人类的上古史,固然大半属于人文科学的范围;同时也是很重要的自然科学研究的题目”,并提出了上古史重建的材料范围包括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地质学、古生物学和历代传下来的秦朝以前的纪载。苏秉琦先生也指出:“一部史前史,既是人类社会发展史,文化史,又是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历史,这种性质决定它必须是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成果,不仅需要吸收人类学、民族学的研究成果,还要借助地质学、古生物学以及许多自然科学或新技术手段。”但目前,多学科协作仍不甚理想,各个学科各自为战的现象仍较普遍,特别是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的合作尚需进一步加强。
四、结语
篇10
青铜冶炼技术起源问题是我国考古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重要环节。近年来,青铜冶炼技术的起源与传播问题成为学术界讨论的一个热点,讨论的焦点一般集中在中原冶铜业到底是本土起源,还是外来影响的产物,以及青铜冶炼技术的传播等。尽管我国青铜器发展史以中原地区为核心,但要全面深入地研究这一问题,必须要对新疆、甘青及中原地区青铜冶炼技术的发展、变迁进行剖析和认识。
目前,时贤已对这一问题提出一些观点和看法。首先,考古发现表明中原地区出土的最早的铜器是陕西临潼姜寨第一期文化遗址中的一块残铜片,距今4500年。但是对这件铜片的存在以及中国青铜器起源的意义,学术界还存在争议,如安志敏认为这项标本,还存在问题,不能作为仰韶文化已经进入青铜时代的确证,并认为仰韶时代中原还不具备冶炼青铜的技术[1]。目前,国内普遍公认的青铜器是在二里头文化的三、四期才大量出现,而反观新疆、甘青、西北地区年代最早的铜器则是新疆地区乌帕尔苏勒巴俄遗址发现的铜珠、残细铜棒4件、小铜块12件,经过检测为红铜,发现者推测其年代不晚于公元前3000年。刘学堂先生认为,中国最早的青铜器群出现在新疆地区的古墓沟―小河文化、林雅文化、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河西走廊的四坝文化中。并且认为中原地区由二里头文化三、四期发展起来的青铜文化不早于北方青铜文化,更晚于新、甘、青地区的青铜文化[2]。李水城先生则将中国青铜文化分为以龙山――二里头文化、齐家文化为代表的东部青铜文化圈,经历了从红铜到锡铜的冶炼发展过程,西部青铜文化圈则以四坝文化、天山北路文化为代表,经历了红铜――坤铜――锡铜的冶炼发展过程,并认为西北地区冶金术的发展要早于中原地区,并通过甘青地区传播至中原[3]。梅建军先生则通过对西北地区距今5600至4000年青铜砷铜的首度发现,提出宗日文化在中原和西北青铜器交流中的重要作用,并认为青铜技术的传播路线还有待进一步的论证[4]。
同时一些学者也提出相反的观点,白云翔先生将西北地区和中原地区的青铜器加以比较指出,两地的早期铜器似乎各成系统,认为两个地区的早期铜器在发展中的过程中的交互过程不完全否定,但主流是各自独立发展[5]。蒋晓春先生则认为中国各地区进入青铜时代没有一个早于公元前21世纪[6]。
综上所述,青铜冶炼技术“西来说”不仅存在争议,而且有待进一步研究。新疆地区的早期先民可能首先掌握了青铜冶炼技术,并经过河西、河湟地区传入中原,并对中原青铜器产生影响。同时,近年来的考古发现证实,河湟地区的青铜冶炼技术可能要早于新疆地区,由此推断,青铜冶炼技术可能首先由河湟地区发端,再向中原地区传播。
二、中原;西北地区青铜器物概况
根据对伊朗、美索不达米亚、埃及等古代文明发生较早地区以及美洲大陆早期金属文化的考察,人类最早是用天然铜(红铜)锻制小件饰物或工具,稍晚时期出现红铜重熔,铸成器件的技术。在这基础上,逐步掌握了还原氧化铜矿以得到纯铜的人工冶炼方法,所得产品质地不纯,比较疏松。中国的冶炼技术和世界其他地区一样,也是从使用天然铜发展到人工炼铜的。在铸造技术上经历了使用敞范、单面范和双面范铸造[3]。
到目前为止,中原地区发现的铜制品,最早的是在仰韶遗址出土的铜制品。见下表(表1):
除了这些主要的铜器出土遗址外,中原地区龙山时代还有一些地区出土了铜器如:山东郊县三里河的铜锥、诸城呈子的铜片、西霞杨家园的残铜锥、长岛县长山岛店子的残铜片、日照王城安尧的铜炼渣、河南登封王城岗龙山灰坑中的铜片、河北唐山大城山的铜牌残片等。但这些遗址中出土的铜器材质各不相同包括黄铜、锡铅青铜、红铜、砷铜,按照世界其他地区的冶铜发展规律我们很难断定中原地区在仰韶、龙山时代已经掌握了成熟的青铜冶炼技术。直到二里头文化时期中原地区才有了青铜文明。有些针对这一现象一些学者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如刘学堂认为:考古学家和冶金史学家依据上述考古发现,经数十年研究无法向众所周知的史前欧洲青铜文化发展史那样,从仰韶文化早期开始到仰韶晚期龙山阶段之间建立起前后相承的中国早期冶铜技术、青铜文化发生发展、繁荣与演化的体系,而且难以将上述新石器时代偶见的铜片、残渣等,当成二里头文化三、四期突然发展起来的中国早期青铜文化的源头[12]。安志敏也在上文中对仰韶、龙山时代出土的黄铜器物产生了怀疑,认为中国到了宋代才出现了冶炼黄铜的技术。因之,从考古学的证据上来看,以二里头三、四期为代表的属于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青铜器,它的开始可能要更早一些。至于中国的青铜器是怎样起源和发展的,还有待于今后的继续探索和深入研究[13]。而反观西北地区,不仅发现了目前所知最早的合金青铜,也是早期铜器发现数量最多的地区。现可将新疆及甘青地区出土的青铜器与中原地区作一对比,西北地区出土青铜器要普遍早于中原地区。
从西北地区出土的青铜器件来看,要普遍早于中原地区,并且青铜数量也要多于中原地区出土的青铜器件。在甘青地区出土的青铜器中甘肃马家窑东乡林家遗址遗址中出土的铜刀,为锡青铜,是中国出土最早的锡青铜。齐家文化沈那遗址出土过一件带倒刺的青铜矛,长度为61厘米,这在早期的青铜器物中是少见的。可见西北地区的青铜技术较之中原地区要较为先进的。在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遗址出土的铜器中经历了从红铜到锡铜的冶炼材质发展过程,这符合一般青铜器冶炼技术发展路线。而中原地区出土红铜较少,有学者认为中原地区是从冶炼青铜合金再到冶炼红铜的,这并不符合青铜冶炼的规律。二里头文化出土的青铜器大部分为锡青铜,从开始就进入了较高的青铜冶炼阶段,从中原地区的青铜冶炼发展历程似乎难以解释。而二里头文化出土的青铜器与西北地区的齐家文化的青铜器有许多相同之处,由此我们不难推断二里头文明的青铜器技术或多或少受到了西北地区各个文化的影响。有学者指出二里头文明的冶金术源于西北地区,韩建业认为二里头青铜文明是在具有兼容并蓄特征的中原文化基础之上,接受西方文化的间接影响而兴起,二里头文化中的双轮车等的出现以及青铜冶金术的发展也应当归因与齐家文化的东渐带来的西方影响。其环境背景则与距今4000年左右的气候干冷事件有关[21]。距今4000年前后的气候降温事件,使得较早具有冶金技术的中亚西伯利亚地区人们向偏南方向扩展,引起了东西方的交流进而通过新疆西北地区影响到中原。汤惠生认为作为位于东西交通孔道上的新疆地区考古文化来说,来自南西伯利亚、中亚、至西亚的文化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不仅是新疆北部的阿尔泰地区或新疆西部的帕米尔地区和塔里木盆地的山前地带的青铜文化深受前苏联的安德罗诺沃文化、卡拉苏克文化、以及费尔干盆地楚斯特文化的影响,即便是新疆东部的吐鲁番盆地、哈密和巴里坤等被传统认为受东来文化影响的地区,其考古文化中也不乏中亚甚至西亚的文化因素[22]。而砷铜在西北地区的出现,也说明了西北地区深受西方冶金术的影响,伊朗地区在BC4000左右就开始使用砷铜,并在以后取代红铜成为主要的金属。在我国西北地区的一些古代墓地和遗址发现有砷铜器物出土,如甘肃河西走廊地区的四坝文化(1900-1600)包括玉门火烧沟、民乐东灰山、酒泉干骨崖等墓地都出土有砷铜制品。此外,新疆东部地区也有砷铜器物发现,位于新疆的尼勒克县已经发现了砷铜冶炼的遗迹[23]。砷铜是第一种青铜合金,人类对于铜器的使用大致经历了红铜―砷铜―锡青铜的技术发展历程,而反观中原地区则较少有锡青铜的器物出现,直接发展到了锡青铜合金阶段,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疑虑和反思。进一步说明了二里头青铜文明的迅速崛起,是在吸收了西北地区已有的青铜冶炼技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中原地区没有完整的青铜冶炼技术的过程,如缺少红铜和砷铜制品的出土的,以二里头为代表的青铜文明从一开始就步入锡铜合金的发展阶段,和齐家文化青铜制品的相似之处,等目前所知的考古遗迹出土的青铜制品的发现和分析来看,关于中原地区青铜冶炼技术的“西来说”是有道理和事实依据的。
三、青铜技术传播新路线
但是,关于青铜技术的传播路线是否仅有新疆―甘青地区―中原地区这一条路线还值得商榷。最近在青海地区同德宗日遗址中发现的三件铜器,为砷铜器,其绝对年代大致在距今5600-4000年之间是中国西北地区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砷铜,而且这也是在青海地区的首次发现[24],要早于新疆东部地区的哈密天山北路墓地和甘肃地区的四坝文化,也早于齐家文化。这就使我们对于青铜技术的传播路线进行重新思考。砷铜除了在西亚、中亚之外在南亚地区也有所发现,南亚印度的Ganges山谷的Copper Hoard彩陶文化公元前第3千纪(出土的金属中,有超过一半的是含砷1%以上的砷铜,D.K.Chakrabrti认为这可能是砷铜的最东界;在随后的位于印度河流域的Harappan文化也有砷铜使用,并且和青铜一起出现[25]。英国学者阿诺德・汤因比认为:人类发明冶金术至今已6000年,是生活在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首开其端,他们制造了杰出的青铜人像和器具;前2900年冶金术传至埃及,埃及人创造性地在青铜像上贴上薄薄黄金,掌握了当时世界上这种独一无二的“高科技”,前2500年传到南亚古印度河上的拉享佐・达罗城,印度人发明了铜焊,他们制作僧侣和铜像,举世无双。他认为历史在其间打了一个盹;他猜测:冶金发达的南亚地域与中国北部的黄河流域之间、长江中上游应有一个人类冶金技术高度发达的重要环节[26]。而这一种要环节很可能就是藏彝走廊,其大体包括北自甘肃南部、青海东部,向南经过四川西部、东部、云南西部以及缅甸北部、印度东北部这一狭长地带。南亚和的细石器曾受西亚的影响,而卡若遗址出土的骨片与伊朗西部克尔曼沙区甘吉・达维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所见的骨片相同,暗示出西亚文化在很早即可能与文化产生过交流[27]。众所周知,三星堆青铜文明与西亚关系密切。而青铜冶金术是否也可以由藏彝走廊到达青海东部地区进而传播至中原。由此我们可以推断青铜冶金术也有可能从西亚―南亚――青海东部―中原的传播路线。这一论断由于出土文物的限制还有待进一步的论证,但并不能盲目否认这一传播路线的存在和可能性。
有此我们可以做出推断关于青铜冶炼技术,不仅仅只有中亚―新疆―甘青―中原这一条路线。还有可能存在西亚―南亚――青海东部―中原的传播路线。这需要考古工作的发现和今后进一步的论证。
参考文献:
[1]安志敏:《中国早期铜器的几个问题》,[J]《考古学报》1985年第3期.
[2]刘学堂:《中国早期青铜器的起源与传播》,[J]《中原文物》2012年第4期。
[3]李水城:《西北及中原早期冶铜业的区域特征及交互作用》,[J]《考古学报》2010年第3期.
[4]梅见军:《青海同德宗日遗址出土铜器的初步科学分析》,[J]《西域研究》2010年第2期。.
[5]白云翔:《中国早期铜器与青铜器的起源》,[J]《东南文化》2002年第7期。.
[6]蒋晓春:《中国青铜时代起始时间考》,[J]考古2010年第6期。
[7]华觉明译《世界冶金史》[M].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5年。
[8]西安半坡博物馆等:《姜寨》,韩汝玢、何俊:《姜寨第一期出土黄铜制品的鉴定报告》[M].文物出版社,1988年。
[9]西安半坡博物馆等:《渭南北刘遗址第二・第三期发掘简报》[J],《史前研究》,1986年第一、二合刊。
[10]任式楠:《中国史前考古综论》[J],《中国史前考古学研究》。
[11]任式楠:《中国史前考古综论》[J],《中国史前考古学研究》。
[12]刘学堂:《中国早期青铜器的起源与传播》[J],《中原文物》2012年第4期
[13]安志敏:《中国早期铜器的几个问题》[J],《考古学报》1985年第3期。
[1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乌帕尔细石器遗址调查报告》[J],《新疆文物》,1987年第3期。
[15]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考古队:《新疆疏附县阿克塔拉等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调查》[J],《考古》,1977年9期。
[16]龚国强:《新疆地区早期铜器略论》[J],《考古》,1997年第9期。
[17]王炳华:《孔雀河古墓沟发掘及其初步研究》[J],《新疆社会科学》,1983年第1期。
[18]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等:《甘肃东林乡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J],1984年第1期。
[19]刘宝山:《试论甘青地区的早期铜器》[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
[20]滕铭予:《中国早期的有关问题再探讨》[J],《北方文物》,1989年第2期。
[21]韩建业:《论二里头青铜文明的兴起》[J],《中国历史文物》,2009年第1期。
[22]汤惠生:《条析与整合―读水涛的《西北地区青铜时代考古论集》[J],《考古与文物》,2005年第1期。
[23]潜伟、孙淑云、韩汝玢:《古代砷铜研究综述》[J],《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00年11月第24卷第2期。
[24]梅建军:《青海同德宗日遗址出土铜器的初步科学分析》[J],《西域研究》,2010年第2期。
篇11
一
设计史教师较高的文化素养有利于对设计史教材的整体把握。设计史课程的特点首先应该是历史,历史学的素养在设计史教学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历史的一般规律性的认识对设计史的学习和研究具有指导作用。古代设计的发展史与古代历史的发展演变的线索、脉络基本上是一致的,尽管设计的发展不以社会性质的变迁和社会变革为依据,但是影响设计发展的决定作用应该是生产力水平的发展和变化。历史上的社会变迁和人口迁移对设计的影响也可以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
从社会和文化的角度介绍设计发展的历史条件,对于正确理解设计发展的内在动力与源泉是十分必要的。设计发展史同这一时期政治史、经济史、思想文化史等方面不是彼此孤立、互不相关的。相反,设计运动的迭起、设计探索的推进,与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演进是分不开的。阿伯特·博姆认为:“传统的艺术史把物象孤立起来研究,把它作为几乎独立存在的现象来对待。而社会艺术史在探索把艺术家和艺术作品置于广泛的、历史的和经济的背景中来研究。”①因此,具有社会历史学的理论素养,就可以对设计史的内容进行高度综合和概括,进而在宏观方面对其内容进行把握。
二
设计史教师较高的文化素养有利于对设计史和设计作品的时代特征进行正确的阐释和评价。对传统文物艺术品及物质文化的学习和研究不仅仅是教学过程中的背景知识,而且还是准确理解和阐释设计史有关问题的必要知识。艺术教育家艾迪斯和埃里克森认为:“有些艺术教员不单向学生展示历代的艺术作品……把孤立的画家及作品和时代、地域联系起来,这样理解艺术史就有了基础。”②归根到底,艺术设计是通过艺术与科学共同的合成手段,创造着人们的全新生活,其中体现的就是一种文化。
中国古代的艺术设计与当时的时代特征密切相关。夏商周的礼制性设计艺术,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关系是其设计的内在根源。中国古代艺术设计的发展变化在许多历史时期都和周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的统治有关,形成了多个时期艺术设计的多元交融的时代特色。这种文化上的多元性特征对当时手工业的发展和艺术设计的发展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在设计史教学中,教师应该对艺术设计史中的多种文化因素进行分析和评价,才能完整而透彻地阐释影响艺术设计的深层次的时代背景和文化原因,学生才能在一个较高的层面上理解当时的艺术设计。可以说,设计史教师文化品位的高低是决定设计史课程教学质量高低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三
设计史教师较高的文化素养有利于设计史文献史料和设计史术语的正确解读。在教学和研究中,设计史课程也要使用多种学科的教学手段和研究方法。
中国古代设计史的内容和材料大多为考古出土的艺术品,对考古艺术品的研究离不开文献史料,设计史学与考古学和历史文献学具有直接的连带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美术考古学所研究的内容有相当的部分与设计史研究的内容相重合,其对新兴的设计史课程的教学与研究的参照作用不言而喻。
对设计史的研究离不开文献史料,而对文献史料的准确理解又需要历史文献学的相关知识,所以,历史文献学对中国古代设计史的研究与教学就显得非常重要。在设计史教学和研究中经常会遇到很多难以解读的史料。因此,设计史教师加强历史文献学的学习是非常必要的。
此外,在设计史教学中还会遇到很多考古学、古生物学、神话学及历史文献学等学科的专有名词和术语,对这些专有名词和术语的解释,关系到学生对设计史内容的正确理解和教师教学任务的圆满完成。鉴于此,对多学科和交叉学科知识的学习和研究,是设计史教师应该负有的责任。
四
设计史教师较高的文化素养有利于对设计思想和设计观念的理论概括与升华。艺术设计包括多方面的内容,既涉及材料、技术,又涉及方法、观念;既是艺术,又是科学;既有人文学科的属性,又与自然科学相关;既有实用功能的限定,又有审美的心理的要求;既有文化的传承,又要求创新。因此,如何对以往的设计思想进行概括与提炼,关系到在教学中能否达到因材施教、深入浅出的良好教学效果。
对设计思想和观念的理论概括与升华,教师必须掌握和了解哲学、美学、宗教学等学科知识。陈乐民先生说:“任何学问就像剥笋一样,一层一层地剥下去,剥到核心,是哲学。”③黑兹尔·康威也说过:“虽然对于设计史不同领域的划分反映了设计者的专业结构,但是在实践和理论中,各个领域之间都存在着很多联系。”④在对待历史文化与艺术传统上,不能采取断章取义的态度,应该从一个更为广阔的视角加以概括和把握。
综上所述,艺术专业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与教师的文化素养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从长远来看,学生的理论水平和创意能力的培养要比技能教育更为重要。设计史是一门多学科交叉的课程,尤其是文史哲诸学科,对这些学科的学习和了解是设计史教师提高文化素养、达到良好教学效果的基本要求。
注释:
①Albert Boime.Art in an Age of Revolution 1750-1800 [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7.
篇12
今年是夏鼐先生逝世三十周年。《南方文物》特辟专栏以追念这位中国考古学的奠基者和领导者。为了强调夏鼐先生在串珠领域的杰出研究,本栏目首次将《古埃及串珠》的第十一章译成中文,以飧读者。此外,本栏目还特意刊出艾婉乔撰写的《古埃及和印度河文明串珠研究的启示》一文,以期引起学界对我国史前装饰品研究的关注和重视。
最后,我们不妨将英国考古学家皮特利爵士前面所讲的那段话略微加以修改,即:“中国西北地区的串珠研究,将是考古学发展的重要课题之一。”(李水城)
分类(Classification)与图谱汇编(Corpus)虽然关系密切,但是两个不同的主题。分类必须系统、标准明确,但只能粗略地划分。图谱可依照日常工作习惯或对象的年代顺序编辑,不必系统化,但要更加具体、详细,以便核对。图谱的结构通常基于分类,为方便查找而略作调整。
考虑到珠子数量庞大,且形式多样,分类是个大问题。与其他科学一样,真正的分类首先要方便、明晰;其次,对已掌握知识能有所概括阐释。第二点远比第一点重要,也更难做到。武断的排序可能便捷,但对知识积累将会形成永久障碍。科学的分类可能不易掌握,且需不断修正,但因为反映了当前的知识水平,将有助于我们理解研究对象,并为今后的发展奠定基础。
珠子的分类有其特殊之处。讨论时必须明确两点:首先,针对珠子,一套合适的分类方案应以有断代意义的特征为依据;其次,分类经过调整,能够比较方便地转化成图谱。尽管整套分类仅依靠一种因素划分不太现实,但正如皮特(T.E.Peet)论埃及陶器分类时所言①,扎实的分类还是要以一种因素为基础,由此形成不同的组,再根据次要因素进一步划分。首要因素应是珠子最基本、非偶然性的特征,而且要显著,这样主体划分才会明晰。
让我们考察时下几种对珠子的分类。首先是培克(Horace Beck)的不朽著作②。他在其中将珠子分为四大类:“规则圆珠”“规则多面珠”“特殊类型珠、坠饰”和“不规则珠、坠”。规则珠子又进一步根据形状而划分――主要是想象的几何特征,完全不考虑材质和技术。而特殊类型――如果除去护身符、圣甲虫和印章,培克的体系实际基于多种原则。有时是形状(如第17组复合型珠子,第19组特殊多面珠子),有时是技术(如第24组细工珠子,第25组粟粒珠),有时是装饰类型(如第46组斑点和眼纹珠,47组条带纹珠子)等等。
篇13
虽然如此,但《人类文明史》的编辑难度仍非一般学术图书可比。首先是它的涵盖内容广泛。以笔者所负责的第一卷《史前与文明的开端》为例,仅这一卷就涉及到考古学、历史学、古人类学、古生物学、古地磁学、解剖学、海洋科学等十几种学科,其内容之繁杂、探讨之深入,绝非普通图书所能涵括。其次,虽然本书翻译专家组给出了高质量的译文,但由于译者各自负责自己的相关学科领域,导致一卷书就有数十位译者共同参与,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学术术语的一致性与译文风格的统一性,也加大了编辑工作的难度。最后,书中除文字内容外,还有大量的图表、表格、地图等,很是考验排版工作的难度。
那么如何来解决这些问题呢?一是求助于各种工具书。除了编辑工作常用的新华社译名室的《世界人名翻译大辞典》和商务印书馆的《外国地名译名手册》外,笔者还借阅了《不列颠百科全书》《大美百科全书》以解决普遍性的概念问题。针对书稿中的考古学部分,笔者重点参考了《中国大百科全书》的《考古学》一卷。至于书稿中的古地质学、古地磁学、古生物学等内容,则参考了《地质大辞典》《石油大辞典》等辞书。为了统一书稿各章中的古人类学术语,笔者找到了1984年中华书局版的《原始社会史》,并阅读了《探寻欧洲史前文明》《剑桥插图史前艺术史》《旧石器时代之艺术》等书籍。通过对各种图书资料的摘抄整理,逐渐规范书稿中的术语用法,也提高了译文的科学性。
二是对各种网上数据库的应用。相对辞书来说,网络数据库的优点是便于检索,从而能够快速、准确地搜集到想要查找的信息。国内的数据库首推中国知网,该数据库中可以查询到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各种期刊、报纸、会议、硕博士论文等文献。对《人类文明史》第一卷来说,《人类学学报》《第四纪研究》《考古学研究》以及各大学学报等都是非常值得阅读的参考资料。书中有些部分参考并引用了国内的一些文献,知网数据库也可以帮助迅速地找到引文的原文,以分辨其正确性。而外文的网上资源,则可以充分利用谷歌学术搜索引擎。